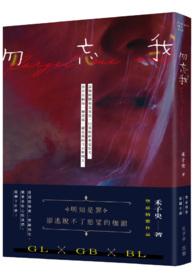富士小说>被虐的反派受总是痴迷我作者海盐屿 > 7075(第14页)
7075(第14页)
瓦盆不破,魂魄不散,爸爸就可以一直留在他身边。
是人还是鬼,又有什么关系呢?沈温瑜放豪言,“那我就给他戴绿帽子。”
嗞……
知了发出平缓而持续的高频白噪音。
禄沧有些纠结,辛斯羽又没戴过帽子,沈温瑜至少要先给他戴上帽子,才能换成绿色的。
但他察觉出还是不说为妙。
沈温瑜心情不太好,挥挥手,“你快进去睡觉。”
转身调头要走,禄沧叫住他,沈温瑜不耐烦皱起眉头,“一天到晚说谢谢,你烦不烦?”
禄沧指指沈温瑜身下的小电驴,“你说有车的时候,我真以为你有车。”
沈温瑜愣了好半晌,意识到禄沧在打趣他,“滚呀,比你的共享单车好多了!”
禄沧已经小跑着进了蒲公英。
天很暗,茂密的植被在夜晚是一团团的黑色,只见一道白色的影子跑到空地上,回头冲他挥挥手。
沈温瑜拧开小电驴,发出开心的笑声。
禄沧轻轻推开门,不大的房间带着好闻的温暖的味道,宁翼的睡姿较出门前发生变化,一条腿从被子里伸出来,背心掀起来,露出软绵绵的肚子。
就连睡觉也皱着眉头。
禄沧在店里洗过澡,换上干净的衣服躺进去,又将宁翼抱进怀里,大约他的皮肤很凉很舒服,宁翼瞬间搂住禄沧。
起风了,树影映在窗帘上不断晃动。
禄沧借着昏暗的光线抚平宁翼的眉头。
破旧的小狗歪在宁翼的枕边,禄沧盯了片刻,伸手拍打了几下,搂着宁翼睡过去。
打烊后的MuClub不像灯火通明时那般富丽堂皇。没有人类施加的作用,只是一栋充满颓废气息的建筑物。
封赫池沉默地坐在包间里,看着灯光一层层熄灭。
桌上摆满酒瓶。
一杯接一杯。
一瓶接一瓶。
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将那句话从脑海里彻底删除。
“只是同学关系,我们又不熟。”
因为不熟,所以不向他寻求帮助。
因为不熟,后面做的事才一件比一件无情!
幸好那位机警的同伴赶来带走禄沧。
辛斯羽陪着封赫池并不多嘴,只眼神欲言又止。
封赫池懒得解释。
后来辛斯羽开始叫他的名字,封赫池想回应,但辛斯羽的脸在他的眼里出现重影。
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鼻涕眼泪蹭了零号一身。零号摸着他的头发沉默了许久,留给他一张写有手机号码的纸条。
封赫池知道零号工作很忙,即使有联系方式,也不敢打扰对方。
直到有一天,邻村那位发烧小孩的家长,听说方建国拿到了县卫生所发放的工伤款,便以方建国去世当天未能治疗、烧坏了小孩的脑子为由,将他们告上法庭,让他们家赔钱。——闻叔叔,打雷了,我想和您一起睡。
有的人在小房间为了论文彻夜不眠,有的人公费出游看遍大好河山。
封赫池表情讪讪,正想再问候几句,盛杨打断他的话头:“零号,病人还在等。”
与此同时,暗暗瞪了他一眼,那眼神,好像嫌他话太多。——不可以。但我可以陪你,等你睡着我再睡。
封赫池朝盛杨的背影比了下中指。
目送二人离去,封赫池忽地想起忘了一件事。早上那仁打电话说姥姥下肢浮肿,穿不进医院的一次性拖鞋,就在网上买了双大码的寄到了招待所,请他来医院的时候帮忙带一下。
招待所那间空房,那仁和那仁妈妈轮流住,昨晚是那仁住的,那仁妈妈留在医院陪床。并不是多麻烦的事,封赫池开车回了趟招待所,取了拖鞋又送回来。
才过去几分钟,医院大厅聚集的人更多了,乌泱泱跟赶集似的。好不容易走到病房通道,发现狭窄的走廊被堵死了,内里隐隐传来争吵声。
“封赫池?”身后有人拍了下封赫池的肩膀,封赫池回头看去,是经常跟在零号身边的护士大姐。
封赫池看了眼对方胸前的铭牌——护士长,石怡悦。他甜甜地叫了声“怡悦姐”。
中年阿姨被叫姐姐总是会很开心,石护士长被他叫得心花怒放,眼角的皱纹笑成一朵花,“远远的看见一个大帅哥不敢认,走近了一看还真是你。”
好像猜到他找谁似的,指了指医院后院,“零号去了行政楼,不在这儿。”
“我不找零号”,封赫池给对方看了下手里的包装袋,“我有个朋友,就是前些天和我一起的藏族高中生,他姥姥在住院,我帮他带点东西。”
不曾想护士长露出为难的表情,朝病房努努嘴:“那难办了,里边正吵着,一时半会儿散不了。”
“吵吵什么?”——闻叔叔,咱们家可不可以养一只小狗。
护士长低声道:“有个病人打完麻醉后休克了,家属正闹呢。”

![女配她刀长四十米[七零]](/img/20691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