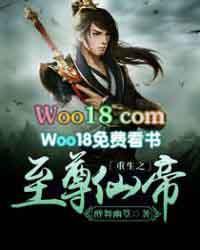富士小说>女附马选段 > 第09章(第2页)
第09章(第2页)
李契静了片刻,道:“世人只看到东宫用尽手段查他,却不知其实他也是孤注一掷在试探东宫。”
萧岑道:“殿下,既已知道这一层就不能再被他牵着鼻子走,臣请高屋建瓴,以殿试之责秋后论罪拿掉礼部遴选考官及出题阅卷的职权,颁布新令组建文兴阁,打破他们原有的规矩。”
李契道:“你说得对,改革绝不能仅仅是换一批人做同样的事,如果怜玉的目的是想做交换,那么孤宁可不要这张投名状。”
萧岑道:“请殿下把这件事交给臣,臣……”
李契道:“但这件事不会太容易,礼部尚书性格懦弱,各党派正是看他好操控所以捧他做一把纸糊的伞,捅破伞面容易,但要拆掉伞骨势必受多方掣肘。”
萧岑道:“殿下,臣等这个机会很久了。”
李契坐下,拿起茶壶浇淋案头的两枚玉石荔枝:“如此孤支持你,不日即请奏组建文兴阁,但有一点,吏部考功即将开始,事关你自己的前程,不要犯错。”
玉石荔枝在茶水的滋润下焕发晶莹的色泽。
萧岑抬眸,收起争辩的态度,恭谨道:“臣迎怜玉去了。”
*
——“罪人怜玉,奉皇太子晋王殿下令指,入东宫侍奉。”
东宫的大门五间三启,绿色琉璃瓦,屋顶垂脊立仙人走兽、梁枋绘彩画,是连华此生所见规格最高的府门。
连华一袭素衣立在门前,身段宛如清水芙蓉。
来往府中的宾客多腰悬金银鱼袋,见到连华,非但不觉寒酸,反恨自己繁冗。
——“没看错,就是传说考过两榜状元的怜玉。”
——“不仅没治罪反而还攀上东宫,真是厉害。”
——“他都换过不知多少门庭了,猜不准为谁办事。”
——“要不怎有那句话呢,怜玉怜玉,愿此生再无遇。”
不时,左边门房走出一人。
连华稍稍打量了眼,交领长布窄袖衫,套着黑靴的脚又宽又大。
——“怜玉公子,老仆是府中管事,你叫我祥瑞。”
连华从袖袋拿出一些碎银,悄压在对方手中:“祥管事大名早有耳闻,曾随殿下出生入死杀过敌酋,也写得一手好书法,今后还请多多指教。”
祥瑞摊开手,平和笑道:“老仆穿这身窄袖兜不住赏,只是秉公办事得验一下符。”
连华连忙拿出云纹玉符,递上。
祥瑞接过玉符,验过之后,意味深长道:“公子,你这块玉符不一般呐。”
连华道:“难道不是东宫的门客都有的吗?”
“不,不,这枚玉符世间仅此一枚,算起来与公子年岁相当。”祥瑞看着连华,目光恍若隔世,“景元初年,殿下的字师从雁留山寻来一块璞玉请大相国寺净水师父打磨成形,将此符献给小殿下,寓意宁静致远。”
连华闻言,摩挲着上面的祥云纹路:“敢问殿下这位字师姓名?”
祥瑞摇了摇头,长叹一口气:“这件事如今不能提了,那位字师只教过殿下两三年,但对殿下的影响极深,殿下现在都还能记得许多他说的话。”
连华跟祥瑞走入东堂,还在想玉符的事,忽见堂中众文士一齐起身相迎。
场面登时熠熠生辉。
因这些衣冠华美的人,东堂左右摆放的珊瑚漆器都黯然失色。
首席之人是太子宾客潘旭,身披鹤氅,腰悬墨玉佩:“怜玉公子,在下崔州潘东阳,闻公子今日入府,特意前来相会。”
——“这位是颍州黄启鹤先生,景元二十一年进士。”
——“这位,芜州门下韩双宏,景元二十四年进士。”
连华一看后面还有好几位衣冠楚楚的人物,顿觉腰疼,索性鞠了一大躬。
——“久仰诸君大名,晚生怜玉。”
众人入座,寻常寒暄。
连华听着席间窃窃私语,径自拿出檀香扇,低眉擦拭扇骨。
场面之下暗流涌动。
潘旭在介绍姓名之时,每人都强调是进士出身,看似无意,但在场偏偏只有一个人是商户无功名,那就是连华。
连华心知,东宫群英荟萃,今后自己若要在此地立足,必先赢下这场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