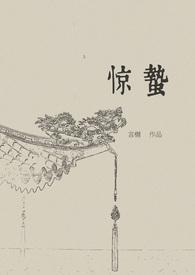富士小说>八零年代娇艳大美人糖瓜子 笔趣阁 > 6070(第21页)
6070(第21页)
她再也不看限制文了,不,秦樾才是不准看的那个人!
岂止是现学现用,分明是活灵活现!
她怎么忘了,能考上国内最高学府,并闯下现今成就,秦樾的学习能力肯定非一般人能及,就连在这方面也是远超凡人。
也不知道是福是祸。
“在想什么?”
耳边传来秦樾低哑的嗓音,紧随而来的就是她咿咿呀呀被撞断的凶狠。
他体力惊人,这都几轮还能有这种劲道。
宋时溪听出他对自己在这种时候走神的不满,哪敢这时候说出那种夸赞他的话?最后遭罪的还是自己。
于是转过头,先是摇头,然后求饶般朝着他伸出手,装作可怜巴巴地喊了一声,“阿樾。”
她微微扬着下巴,浑身上下都泛着羞涩的潮红,发丝早已散乱开来,黑发白肤,愈发楚楚动人,也衬得那些绯色印痕愈发明显。
那只手因为撑在台面的时间久了,通红一片,跟她这个人一样,惹人怜惜。
阿樾二字从红唇边溢出来,令他心燥难耐,眼尾潋滟上一抹薄红,暂时停了下来,然后放柔力道把她抱起来放在台面上坐着,舍不得再让她出半分力气。
知道她喜欢,他半跪下去,卖力伺候。
没想到喊一声阿樾,就能换来这样的享受,宋时溪有些后悔没多叫几声,但也有可能叫多了,就不管用了。
抓住他稍许刺挠的短发,整个身体都放松下来,但是又忍不住紧绷,没多久就去了。
她娇滴滴地趴在他的肩膀上,眼波流转,含糊着说自己累惨了,让他放过她,赶紧休息。
“小没良心的。”秦樾差点儿被气笑,她倒是舒爽了,完全不管他。
宋时溪心虚地抿了下唇,小声道:“你自己有手啊。”
“……”
秦樾哀怨地垂眸看向她,他刚有所动作,她就立马钻进了他怀里,怎么说,怎么哄都不肯抬头,铁了心地不肯管他。
这是他捧在手心里的女朋友,对此,还能怎么办?打不得,骂不得,只能宠着,顺着。
秦樾揽住她的腰,扯掉束缚,开始自给自足。
只是那手时不时就连带着一起有意无意地蹭过她的大腿,让人忽视不了他在做什么,宋时溪听着他剧烈跳动的心跳声,脸后知后觉地滚烫起来。
等他结束,两人才开始洗漱上床睡觉。
第二天宋时溪醒来的时候秦樾难得还在床上,像个大火炉一样牢牢禁锢着她,就算开着空调,她都觉得身上出了一层薄汗,但是她没舍得推开他,甚至还往他怀里钻了钻,唇角往上勾了勾,喜欢极了这样的事后早晨。
她刚动,秦樾就感受到了,两人都不着寸缕,紧紧贴在一起,实在为难老干部。
他手掌动了动,顺着腰线,掠过平坦的小腹,试探性地抠进去,哑声问:“疼不疼?”
宋时溪并拢双腿,将他继续的路线拦腰截断,颊边泛上粉红,轻哼道:“疼……”
语调上扬,分不清是真是假,但秦樾刚犹豫着收回手,就感觉她抬起屁股和腿,往他身上坐了过来,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了个东西,得意洋洋地在他眼前晃了晃。
秦樾呼吸一滞,眼睫颤动。
接下来度过了他有记忆以来最欢愉的晨光。
荒唐完,两人一起下楼吃饭,宋时溪坐在秦樾旁边,借着刚才自己都把力气用完了的理由,让他一口一口喂给自己吃,她则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看电视。
现在的港城电视节目可比大陆丰富得多。
秦樾还是第一次这样全程给人喂食,动作稍有些僵硬,但是眉宇间却全是笑意,显然是乐在其中,等吃到一半,就完全上手了。
给她喂完,他才开始吃。
本以为她能陪着,谁知道他刚抬起筷子,她就拍拍屁股走人了,窝进更舒适的沙发,半躺在里面,时不时笑得前仰后倒,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秦樾咬了咬后槽牙,觉得有些牙酸。
等他吃完才发现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难怪这么久没动静,秦樾轻手轻脚地抱起她,刚碰上去,她就朝着他靠了过来,睡得泛红的脸颊还在他手臂上蹭了蹭。
见状,心里所有的小情绪都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
宋时溪这一觉睡了快四个小时,正值下午,外面晒得很。
秦樾不在身边,也不在书房,问过保姆后才知道在她睡着后没多久,他就出门了。
她没事干,窝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电视,又看了一会儿杂志,外面突然响起了汽车的声音,宋时溪还以为是秦樾回来了,当即惊喜地探出头去,却在瞧见来人后,有些失望地嘟了嘟嘴。
但很快就调整了情绪,笑着打招呼:“赵助理,你怎么来了?”
赵河彩是个很心细的人,她没错过宋时溪脸上一闪而过的失望,猜到她是把自己当成了秦总,连忙道:“秦总下午去跟景信的人吃饭了,让我过来接您。”
“他们这时候早吃完了吧?接我去干什么?”宋时溪眨了眨眼,不解地皱起眉头。
“不是去吃饭,是参加酒会。”
通过赵河彩的解释,宋时溪这才知道今天是梁民池父亲的生日,也就是现在景信集团真正的掌权人。
这样的人物过生日当然不可能低调,几乎请了港城所有有头有脸的名流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