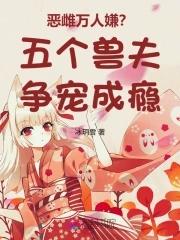富士小说>凤谋锦绣人物介绍 > 第161章 欲填沟壑为疏放VIP(第3页)
第161章 欲填沟壑为疏放VIP(第3页)
这一边,泰王府内。
李起云刚刚被“准许”离开那座幽闭偏殿。
数日未见天光,他整个人消瘦不少,眼底的血丝像枯枝丛生,整个人带着压抑的疲倦。可他一回府,连茶水刚送到手上,还未喝了一口,前厅的侍从就跌跌撞撞跑来报信。
“殿下丶殿下!……圣旨已下,太子已定——”
李起云回头,看到了张向天也站在门外,神色肃然。
“谁?”他嗓音沙哑,却急促。
“……晋王李起年,封为太子。”
那一瞬间,他手中茶盏“啪”地落地,碎成几瓣,滚落的茶水在台阶上浸湿一片,像是血一样地蔓延。
他输了。
他……输了?
与此同时——
徐圭言正在书房中,听着一名机要亲信快步而入,带来消息。
“太子已定。”那人说,“长公主丶李相皆出席朝议,陛下亲口宣旨,封李起年为太子,明日颁告百官。”
她没有立刻回应,指尖在书案上一点一点轻敲,像是在思索丶也像在计数。
许久,徐圭言叹出一口气,转头望向窗外,远处楼阁间隐隐传来宫钟之音。
她忽而想起冯知节,想起他跪在殿前的身影,想起他离开长安时,沉默不语丶目光冷冽的样子。
冯知节被清出局,这只是个开始。
皇储确立——朝局重构。
徐圭言没有赢的感觉,她低头看着手中的书卷,一字都看不进去。
而就在旨意传下的当夜,东市里有个老艺人喝得大醉,在酒楼角落自言自语:“冯将军走了,太子定了……可你们都不知道,真正的乱,还在後头。”
话音未落,他突然闭口不言,跌入昏睡。
不知何时,长安城内流言四起,“太子者,非真龙也。”
圣旨已下,金銮殿上,玉玺封蜡尚未冷透。
东宫尘封许久的宫门重新开啓,李起年身披暗金织凤的太子朝服,在徐圭言与礼部尚书陆明川的引领下,跨过那一段玉阶时,他的脚步无比稳重。
他低头看着那层薄雪与残霜交错的地面,仿佛看到前人的血影在石缝中未干。
徐圭言被安排到东宫一旁的小院中办公。
那是先帝早年为太子亲信设置的文书院,光线幽暗,却背靠御花园,是座静谧的所在。
她推开厚重的木门,案几上放着新送来的政务卷宗,未揭封的信札堆成一叠。窗纸被风吹得颤动,一缕阳光照在她沉默的面容上——她知道,从此再无退路。
与此同时,京中开始散播出一则消息:李起凡病重致死。
无风无浪,无人在乎,只有後宫中冷凄凄宫殿内的沈皇後,守着夜色,守着寂寞。
但更惊人的消息来自西南边陲。
冯知节被调离的圣旨传至边疆後,不出三日,吐蕃边界大乱。
原先龟缩不前的敌军忽然突袭四镇。他们不惧将军印,不惧朝廷旨意,却惧冯知节的刀锋。军中将士哗然,有人夜里以盔甲枕席痛哭,有人写血书请冯将军复任。可冯知节此时早已踏上南下之路,听着马蹄声在梦里远去。
这日午後,皇宫昭德殿内。
李鸾徽身披玄袍,端坐于榻後,神情疲惫却强撑着精神,案前放着厚厚一摞名单。他手中缓慢翻阅,嘴角偶尔抽动,像是在咀嚼什麽难以下咽的名字。
李慧瑾披着长公主绣金的朝服,恭谨地立于案前。她已经陪皇帝议事一下午,直到夜色吞没窗外的芙蓉瓦。
“你觉得徐圭言……给太子当宰相如何?”李鸾徽忽然开口。
眼下正是组建东宫要员,为太子搭班子。
李慧瑾愣了一瞬,旋即答道:“她有才干,有胆识,兼有阅历,重要的是,她为天下百姓着想。她,很好。”
李鸾徽沉吟。他指节用力,扣在案几之上。
“但……一个女子,当宰相……朝中老臣们,怕是难以接受。”
李慧瑾轻声一笑:“陛下,武帝为女,仍立千秋;上官婉儿辅政,亦未乱大局。天下在理,不在性别。”
李鸾徽的脸色骤然冷下,啪地一声,将名册狠狠扔在地上。
“够了!”他咳嗽不止,胸口急促起伏。
李慧瑾惊惶失措,立刻跪下:“臣妹失言,请圣上息怒!”
咳嗽声在空殿中久久不止。李慧瑾从地上擡起头,望着哥哥那张因李起凡之死而日渐枯槁的面容,心中忽然一阵悲怆: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帝王,如今却被过去的阴影和现实的重压拖成了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