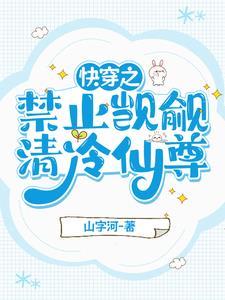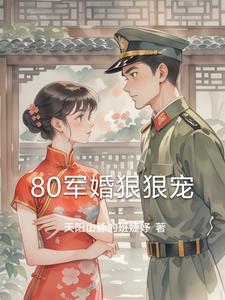富士小说>觉得挺值的 > 百年河妖(第2页)
百年河妖(第2页)
“是,师父。”谢远乖乖地坐回凳子上。
而璟央则深深叹了口气。自百年前,便有一股郁闷之气压在他心头,教他事事装作恍若未闻。就算在天界做仙君也不自在。如今这一桩桩被人挖了出来,他倒觉得畅快了不少。
他又自嘲地笑了笑,若知今日如此,当初早早拒了晴月,或是自幼就入了道观,不,不应该入道观,应是按照普通人的人生行迹去参加会试,或许便不会陷入今日这般局面。
若是谢远能听到他心中所想,定然会骂他,按照他这种做事犹犹豫豫,不反对也不拒绝,什麽好事都想得到,什麽义务都不想履行的性子,任何日子都不会好过。
当然谢远不知他所想,尘渊也自然不知。
事到如今,还是先找到死婴较为重要。尘渊起身对璟央道:“我与阿远准备去那几个小城看看,你是与我们一道还是留下善後。”
璟央回道:“我留下来吧。”
尘渊见状,也不再多言,唤上谢远便啓程赶往西边的临城。找了个无人的角落,尘渊施展瞬移术,二人顿时出现在临城城门下。
谢远擡头望了一眼城门,问道:“师父,你为何让璟央独自留下?你不怕他跑了吗?”
“阿远,他引我们入那个小镇就意味着他也不想再躲避了。”尘渊耐心解释道。
谢远颔首道:“也是。”随即他便不再思量此事,而是擡头仔细打量着城门。
高大的铜门上面锈迹斑斑,应是经常在水中浸泡所致。城楼上的牌匾却是崭新明亮,在日光的照耀下,璀璨夺目。
城门处有官兵在例行检查入城人的文凭路引。谢远环视一周,见这里的百姓并没有想象中那般疲于奔命,反而一副安居乐业之态,轻轻笑道:“看来,这五年给了临城喘气的机会。不过,师父,那河妖为何从未怀疑临城,反而一直在报复芜城?”
见尘渊盯着城门半晌未回应,谢远扯了扯他的衣袖,唤道:“师父?”
“嗯。”尘渊应道,“我方才用神念问了河童,她回道是因为偷走孩子之人留了一方手帕,上面写道‘今吾取走汝子,望汝切勿再以活婴填江’。故而,她认为是芜城之人做下的。”
一方手帕,短短两句,道尽了为人父母的辛酸。百年间,芜城已有百名幼儿葬身江底。虽说在历史长河里,多少婴孩未到成年便夭折魂归冥海,父母虽是难过,但随着岁月流逝,总能抚平心底伤痕。但若是被扔进江底饲养妖魔,爱子如命的父母总归是意难平。
晴月也是为人母,故而她以为是芜城家有婴孩之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孩子被选中,故而铤而走险偷走她的孩子。
但谢远却不这麽认为。他望向城楼上的牌匾,暗暗思忖,连一位仙君都找不到的死婴能藏住哪里。
思量间,师徒二人已通过官兵的审查走进城内。
城内主道两侧的房屋虽然还残留一些残垣断壁,但多数都是新建的瓦房,屹立在日光下,让这座小城如获新生。沿着主道走了许久,观望了半晌,谢远不由出声问道:“城中凡人以前都住在哪里?难道也如芜城那般,住在山丘上?”
尘渊指了指远处耸立的高台,道:“我们去那边看看。”
待走近以後,谢远啧啧乍舌,连连称赞:“真是大手笔啊。”可不是嘛,一般城中也会设高台,但多为祭祀祈福所用,不会超过五丈,然此座高台却有二十来丈,占地有百亩左右。高台四角皆设了台阶。
二人拾级而上,谢远时而轻叩石壁,时而触摸石壁上的青苔,一路划过。尘渊温声提醒道:“仔细划到手。”
“无碍。”谢远朝他笑了笑。
台阶很长,足有百馀层,教人不难想象其建造之艰难。
台阶最高处也有官兵把守,他们皆面露凶相,对师徒二人高声喝道:“这里不欢迎外人,还请二位哪里来的便回到哪里去。”
尘渊淡淡扫了他们一眼,几位官兵随即双眸迷茫,恍惚了片刻,方恢复清明,躬身行礼道:“原来是县太爷请的贵客,这边请。”
有城兵引路,二人一路顺畅。途中,谢远环顾四周,只见这高台之上俨然被打造成临时的避难所,一座座茅屋散布四周。如今这茅屋皆是空的。
临城百姓显然是已搬回原居所,这高台便空置下来。
然依这城兵之言,此次的县衙似乎还留在这高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