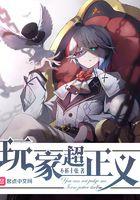富士小说>临江辞免费阅读 > 第五章 青天焦土(第1页)
第五章 青天焦土(第1页)
第五章青天焦土
伴着一阵清朗明快的鸟鸣,一缕晨晖透过窗棂,照在花色暗沉的红木架子床上,扰醒了睡得四仰八叉的少女。少女揉了揉眼睛,伸了个懒腰,趿拉着短靴走到窗前,望了一眼窗外的日晷。
糟了,现在已是巳时了!起晚了整整一个时辰,等下见了先生怕是又要被罚抄书。少女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兜上靴子,翻梳子和头绳的时候不小心碰到摆在桌上的包裹,愣了一瞬才发觉,自己正被扣在行宫里,离先生不晓得有多远。
她跌坐在床上,用手指简单捋了捋头发,极其随意地一扎後便拎着包裹出了门,走了约莫一刻钟才找到一处干净的活水。就着水洗了把脸後,她从包裹里摸出一只铜壶和一盒火寸条,收集了些枯枝,架起盛满水的铜壶准备烧这半日用的开水。
这处行宫位于半山腰处,风景秀美环境清幽,只是看样子已经荒废了不少年头,所有空地都长满了齐腰深的野草杂树,深秋时节来此,目之所及一片枯槁色。刚被送到这里时,她发现好些房屋背阳的角落里都生了菌子,屋里也都落满灰尘,有些光线不大好的屋子,还透着一股子霉味。
背着炊饼和腌菜转了大半晌,她才找到几间勉强可以用来休息的卧房,在房间里又搜罗了好大一番,才找齐这几日要用到的物什。
行宫里的东西,一件比一件精致华丽,到处都镶金嵌玉雕龙画凤,就连一只普普通通的杯子也要描上细致繁复的金边。这盒火寸条是她在多宝架上翻到的,原本装在一个凤纹描金檀木匣里。刚打开那只匣子的时候,她还以为这里的人终于节俭了一把,火寸条下面垫的是白色粗砂,拿到阳光下一看,哪里是什麽粗砂,分明是大半匣白玉珠子。
不过一座废弃的行宫,其中物件便如此奢靡;那偌大一个皇城,每日的开支用度,又该有多少呢?
还在山里时,她便见过不少找先生治病却连药钱都拿不出手的穷人,进京这一路上,又见到不少流离失所的难民。先生告诉她,地方上给难民施粥时,往往会在白米里掺进白砂枯枝。这世上,有人将白砂做白米,有人将白玉做白砂,前者作假,後者弄真,真真假假之间,苦的唯有平头百姓。
不知不觉间,铜壶嘴部已经开始冒白气,小商取了两块炊饼摆到壶盖上。不多时,壶中泉水烧滚。她小心翼翼地取下有些烫手的炊饼,又将滚水往早已备好的瓷瓶里倒了一半,刚好装满瓷瓶。摁紧瓶塞後,她从包裹里取出两只小碗,一只用来装水,另一只则斟酌着分了点腌菜进去,就着白水和腌菜,她啃完了手里的两块炊饼。
以往的时候,先生几乎从不让她进厨房,只要他在家,一日三餐便都是他下厨。也就是他外出做事的时候,才会留下足够的食材,让她自己随便做点东西填饱肚子。一来二去的,她做饭的手艺就生疏了许多。明明是七岁就拿得下各种家常便饭的人,现在焖碗米饭都可能焖出夹生饭。
只是现在的条件,她即便是想焖夹生饭,也没有米给她糟蹋。满屋金玉又如何,流落在外的时候没有一件用得上。往日里她还老是嫌弃先生做饭来来回回就那几样,不曾想现如今,她连炊饼和腌菜都要精打细算着吃。
不知道先生此刻在做些什麽?先生平日里卯时便起,到了这个时辰,应该早就用完早饭了。
也有可能根本顾不上吃饭,正忙着为她和李凤交涉。记得十岁那年,她跟着村里几个同伴跑到山上找灵芝草,中途碰上大雨,为了避雨几个人躲进山洞,结果雨倒是没淋透,雨停了出去发现没人记得路,一群人心都凉透了。
当时先生和村里几个大人一起,找了他们一天一夜。找到他们时,先生衣服上被树枝划了几道口子,衣袖丶衣摆和鞋面都沾满了泥污,见了她先生没多说什麽,只是检查了一遍确认她身上没有伤口,就把她背回了家。
错误太过严重,一通罚当然是免不了的。到家以後,先生直接将她拎到书房,放了厚厚一沓宣纸在案上,要她抄满五千字的礼经。
这次虽然又要先生来找她,却应该不至于最後被罚抄。毕竟让她闯阵是先生做的决定,把她软禁又是李凤干的事情,她从头到尾都只是个帮衬的配角。只是那李凤如此蛮不讲理,不知道先生对上他会不会吃亏。
毕竟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李凤若是好相与,先生早把她接回家了,哪里用得着等到今天?
虽然邹大哥他们都说先生精通阵法,可李凤也是动动手指就能炸掉一座假山的人,先生落在他手里,能讨到好去吗?再加上社稷坛又是李凤的地方,但凡他随便做点机关,派几个人埋伏在周围,先生就会完全处于被动。
小商越想越担心,手上收拾东西的动作都慌乱了几分,以至于完全忘记身後还有一堆滚烫的热灰。忽而一阵西风扑面袭来,将身後热灰尽数扬进草丛,火星撞上枯草,顷刻碰出橙红的烈焰,一窜便是一丈来高,想去扑灭已经来不及。
所幸她刚才便以泉水为中心,清出了二丈方圆的空地,周围又没有房舍和树木,只有一片根根直立的白草,再往外便是铺了石板的地面,火应该烧不到别处去。为防方才的惨剧再度上演,小商拎着铜壶奔波在水源和烈火之间,往草上火上灰上浇了不知多少趟水,累得腿都擡不起来,好几次还险些被火伤到。
虽说到最後也没能控制住火势,却也基本解决了馀烬。喘息之馀她看向四周,才发觉杂草已然燃烧殆尽,只剩了一地湿冷的残灰,映在蓝天白云下,空旷暗沉如书中描述的古战场。忽有雁阵掠过长空,瞬息後又没入层云。
鸿鹄来去,草木荣枯,所谓万物皆有轮转之道,果如是乎?青天焦土之中,浮云群雁之下,一方石碑赫然耸立,上书三个古体篆字——天地冢。
石碑不高,仅达小商腰部,方才不曾发现,想来是因为没入了草丛。只是偌大一个行宫,单留这麽一片空地,又立了这麽一块稀奇古怪的石碑,着实有些令人费解。
怀着满腔困惑,小商走近了石碑。石碑看上去比这处行宫年纪大得多,棱角处皆有严重磨损,有些地方甚至有了裂痕,仿佛经历了数千年的岁月冲刷。除却那三个大字,碑上再无其他装饰,不仅丝毫不显单调,还添了几分古拙之气。
因为年代久远,她看不出碑文雕工如何,仅能看出三个篆字布白严肃笔力遒劲,远望过去,颇有吞吐山河之势。
常言道字如其人,先生也擅长篆书,写出的字却和石碑上全然不同。先生的字严整之馀还带了几分俊逸,既有士子之风又有隐者之意;碑上的字却浑厚宏伟,运笔之人当是位雄才大略的君主。
揾着石碑上的字迹,小商回想起先生那句:“字要写自己的,学问也要做自己的,我的字你学不成。”
往日里先生总是批评她的字里没有自己,只晓得临他写的帖子,临又临不出个样子,笔下只得三分皮肉,不见半点风骨。彼时的她毕竟年幼,尚不知天高地厚为何物,丝毫不能接受如此直接的批评。在她看来,自己的字分明和先生的一模一样,又怎麽能说全无风骨?
见她如此,先生也不再坚持,只是抚着她的头发笑着说,待你再长大些就明白,字和字的区别在何处了。如先生所言,到了及笄之年以後,每每再见当初那些稚气未脱的字,都会联想到自己那时的大言不惭,以至恨不能羞到地缝里藏起来。
可尽管知道了二者不同,她却始终不懂是何缘故。就好像做学问,自八岁被先生收养以来,她便一直受着先生的悉心教导。积年累月下来,经史子集加在一起,少说她也读了一二千卷。
可每当她问及先生自己可否算作才之秀者,先生都会一笑了之。问得多了,先生便抛一道题出来让她解,先生随口一问的东西,她往往要翻上半个月的书才能找到答案。虽说一来二去的,她也解得自己同先生差距之大,却一直不明白自己究竟差在哪里,明明先生问的题目,答案都在她看过的书里。
见了这块石碑她才明白,她和先生的差距,从不在书文之中。就像石碑上的字她写不出一样,先生的字丶先生的学问她也学不来。先生到过的地方她不曾到过,先生见过的人事她也不曾亲见,故而她练上一辈子,也不可能参得透他字里行间所现之风骨。
不过也是,若是读上几本书便能参透先生的学问,先生岂不是枉活这许多年?如此想来,她似乎也不用担心先生在李凤处受委屈,他晓得那麽多东西,即便是被李凤刁难,也一定想得到如何应对。
想通这一点,小商整个人都放松下来。她又看了一眼前方的石碑,先生若是见到这方石碑,会说些什麽呢?
大抵会在感慨一番後,讲出一段它背後的传说故事吧。先生研究过大梁各个州县的方志,他们这次进京,每到一个地方,先生都能将那里的风土人情奇闻逸事说得头头是道,让他们涨了不少见识。
为了有个正当理由听先生讲故事,她折回去寻了块黑炭,又跑到附近的屋子里扯了段白绢,覆在石碑上一笔一划地拓印起来。不曾想拓到最後一笔时,她脚下骤然一空,跟着便直挺挺地掉了下去。
![你放开我家女配啊[快穿]+番外](/img/6583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