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小说>姻缘殿人物介绍 > 月老与亡人(第1页)
月老与亡人(第1页)
月老与亡人
126月老与亡人
阴雨日,已处傍晚,天色尤为昏暗,恰是正好,只可惜看不清她深衣是何颜色。她手撑伞,不肯再近一步似的站在院中,两年前的安愐候府,他也曾站在同样的地方,一手撑伞一手执雁,生怕逾礼,误了纳彩。
“昨日,车上所坐,何人?”
她的声音裹在秋雨里,冰一般冷,被伞遮住的脸,若他走下阶去或许看得到,可他不能,他不敢。
“将为吾妻之人。”
“汝何人?”
“杨亡也,隶军中校尉。”
“可识我何人?”
“安愐候府女公子也。”
“可识我何人!?”
“吾故友胞妹也。”
“可识我…何——人!?”
“吾…客也。”
她的伞忽向上擡起,露出星眼一双,她哭了,第一次,被他伤得哭了。
“杨校尉可记得自己另有婚约?”
“自然记得,退婚之景历历在目。”
“你当知那不过权宜之策!”
“女子不易,女公子顾虑前路,于彼时退婚乃情理之中,如今因我有迁,推说权宜,亦可理解。若我尚无婚约,大可相商。然,亡既已订婚,贤妻良善无缺,我又何能薄待?”
“良善无缺,自是强我百倍,我于此从无矜诩!校尉又何必挖苦?”她从小到大,经历过太多抛弃,却独独此时,心中似别有天地混沌未开,只等此刻天崩地裂!万物尽可恶!她扔掉了伞,死死盯着雨帘泪幕後那悠然檐下鬼魅般的黑影,看不清脸,更看不清心。唯恨然道:“我心如何,你再清楚不过!何须这般?彼时彼景,难不成我痴缠不放许你生死相随,他们就会放过你?还是只要我赌咒发誓信你清白待你荣归,你就能活下去?你若有苦衷,我愿与你共担。你若打定了主意与我陌路!但说无妨!我无强助只能,亦无痴挽之欲!然无论你认与不认,终究是我救你一命。就算不够生世感念,也足值你一生亏欠!”
言罢,转身。
过去,她总觉亏欠于他,“望再有相见日,有缘偿君恩。”又怎单单是借车之恩,冷漠丶忽视丶针对,这些与“家”连带的感受尽因将归家而连番袭来,她怯怯不安却要强装无恙,是他的温善如初秋暖阳,像一种征兆,代表着一种转折,似预示着一个开始,一段与过往截然不同的新生活,让她有资格向往,去面对丶去追求。儿时未吃到的蜜饼,他让她吃到了腻,城墙上的糍糕恰在她最空的心上粘满了星星,春日的芽苗,纳彩时的笑……就算长兄远居都城,就算家中尽是冷脸,都无碍。只要有他,便尽圆满……
“女公子可将马带走。安愐候盛情难却,然枫儿本无意索马。”他看着她的背影,自以为镇定,却全不知自己何时走下了台阶。
门口的白马,她来时便觉眼熟,原就是长兄为她买的那匹,可怜它在雨中不知淋了多久,不耐烦地想要逃离,却又被牢牢困在原地。茗朏犹记初见它时的欣喜,可她没认出它,它也并不识主,想必它也更喜爱幺弟一些。原来父亲又将它送予了杨伊未来的妻子。盖是对杨家有愧之故,亦或不愿再睹物思人。苦生处处牢笼,岂骑良马可逃?她曾向往的跑马的肆意是杨伊给的,而今空留马何用?“还你了。”她已无力回头,声音唯秋雨闻。
雨落滂沱,似是自两年前那日一直下到了今天。
“郎君怎这般站在外面?”凌凌不知自何处归,虽撑了伞,却不比杨伊强几分。
“她来过了。”
凌凌本已将伞送到杨伊头上,听见此话又收了回来。“女公子自小缘薄,受尽冷落,虽最和善,却极难笃信丶依赖何人。你此举,已与杀她无异。你活不成,偏要她也死吗?”
“我既无力护她生,至少该送她死,总好过将她困锁身边日日求死。”
“如此说,倒还要赞君高义了?君既有义,何不放我生?”
“我既念死,不可无碑。怪只怪你时运不济,陪我走了一遭冥府。”
凌凌苦笑,“郎君待我果真是没有半点愧悯啊!”转身上了台阶。“也就休怪我拉人做鬼了。”
杨伊一时慌乱,生怕她对茗朏说了什麽,转瞬清醒,追至廊下,问:“你见了江原?”
是啊,她见了江原,即便他说过要将他留在茗朏身边,她也还是去见了他,说了不该说的话。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报复,报复他既不放她归侯府,又不为她赎身契,报复他让她成了逃奴,青梅竹马不相见。可这却是一种伎俩,一种她与杨伊都已习熟的强装恶人的伎俩。他们似已成了不做恶就无法生存的人,似成了恶鬼,似密受监视。明明没做错什麽,可却每一件事都是错。
当初她答应随船同行,本以为十天半月便可归,可她未料杨伊已伤得这般重,却仍拦不住他执意赶路。她领了世子的嘱托,便不能眼见着他死,又生怕被人发现踪迹,不敢留下讯息,只能跟着他,想着等他的伤基本恢复了就回去。可路途坎坷,他的伤反复难好。她本以为他要入都,却是一路到了上原。上原郡守乃杨父挚友,杨伊于此落脚,她本可放心而归,可她总疑郡守不可靠,便多留了两日。怎知两日後郡守竟那般和盘托出!她本不过寻常渔家女,入侯府为婢讨生路,哪里想过要参与这些家国大事?可当真听了,家国又岂是他人的家国?被抛弃的上原被十万衆,哪个不是如她一般只为讨条活路?
“去岁已是不好,今夏旱情更重,郡中收粮仅不足所需三成。”起初曹郡守只是询问杨伊今後打算,又提起与杨父旧时光景,感叹世道不公,说着说着,忽如早有此意,又似脱口而出般道:“赈灾之请自初秋起呈,至今不下三十道,未见片言复。上原冬寒栗骨,若再无赈粮,恐有相食之势。曹某无能,别无他法,只能以官佯匪,于郡外设伏,每有富户途径,各取其粮资半,以资购粮,入夜而分。然虽有微效,亦不过杯水车薪。无奈,曹某既已舍君子道,便索□□行偷盗之举。本已有谋,怎料刚出南门竟遇一粮队。其人受劫後全无抵抗,愿将所持尽数交予,唯道‘求见郡守’。我自知佯匪之事已然败露,想左不过一死,见又何妨?遂坦然以对。却未想此人竟是为劝反而来。”凌凌初听“劝反”一词,相比于惊讶,更疑惑“是何人将返何处?”直到郡守又说“那人留有一封信,嘱我若决意同行,则展之;若非,则毁之,全当其只为送粮而来。虽我已堕匪盗之流,然所涉之人有限,不日事发,亦可以受我相逼为由为其开脱。可若反,战不可免,死伤或远甚于灾。”凌凌这才恍然明了,此“反”非彼“返”。惊叹此等大事怎可随意与旁人说?暗察杨伊脸色,只觉悠悠然似已有决断。“然若不反,今冬过後,死于饥馑之人难料几何。若再逢灾年,又当如何?我反与不反,死伤不可免。但若反,必需明主。我思此人以粮相挟,恐难为仁君。遂本不欲与之谋。此为六日前之事。我反复思索,数次举信欲焚,总有不决。适逢伊至,闻杨兄罹难,悲愤而饮,酒後莽而展信,却见内书‘君子仁义礼智,郡守所行至仁,馀所钦佩也。故不忍见君自舍忠义,遂以赈粮相挟。自知非君子所为。然今旻天疾威,王微臣重,四国无政,谋臧不从,已远非君子堪挽。若为天下济,馀为奸鄙亦何妨?喜君愿同行,以君之德美,谨馀之言丶审馀之行,毋有偏差,恪守本心。乃馀之大幸也。另,赈粮将于辜月朔日前至,无论君展信与否。’”
郡守为自己的揣度羞愧不已,引书信人为知己,大受鼓舞。可凌凌却只觉惊错——初入上原时,虽感异样,但因一路逃亡,无人可信,也便未能将这异样归为灾情,且後来再未出过郡府,亦从不觉缺粮少药,竟不知灾重已至这般。可她虽同情万民饥苦,谋反之事也实在重大,怎能不担心今日听了这话,若不与之同伍,明日是否还有命可活?正心焦,却听杨伊问:“叔父可愿替伊举荐?”
“我与你谈起此事,正是存了这个心思。杨兄之仇不可不报!可如今朝中,既能视灾情若无睹,又岂会秉公审理此案?多半拼死伸冤也只落得个自赴罗网罢了。且此人不仅胸存大义,且身份高贵,举国上下鲜有可比。虽偏安一隅,却军粮皆足。虽未明言,但此次相助定也是看中了上原碳铁。欲举兵之将,有此谋划无可厚非。若伊无悔,我便予你十车长刀五车羽箭先往,以表上原心意。”
“何日啓程?”
“此事极秘,断不可冒失。我料应有心士与赈粮同至,待与之谋而定。你且安心养伤。”
“郎君当真要与之谋?”凌凌待郡守走後问,盼他只是虚与委蛇。
“此事你全当未闻,万不可与旁人说。我会尽快送你回阳湖,待归去…只说我已死。”
“谋逆之事何其隐秘,怎会轻易泄露?郎君就不担心是圈套?”
“圈套也罢,利用也好,我如今伸冤无门,总要闯出一条路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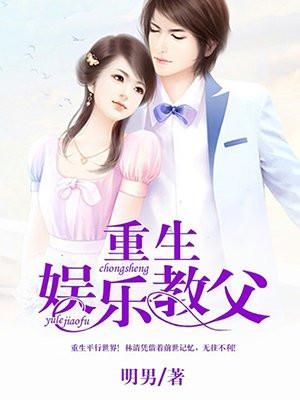
![我拿你当哥哥,你却想…[穿书]](/img/4388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