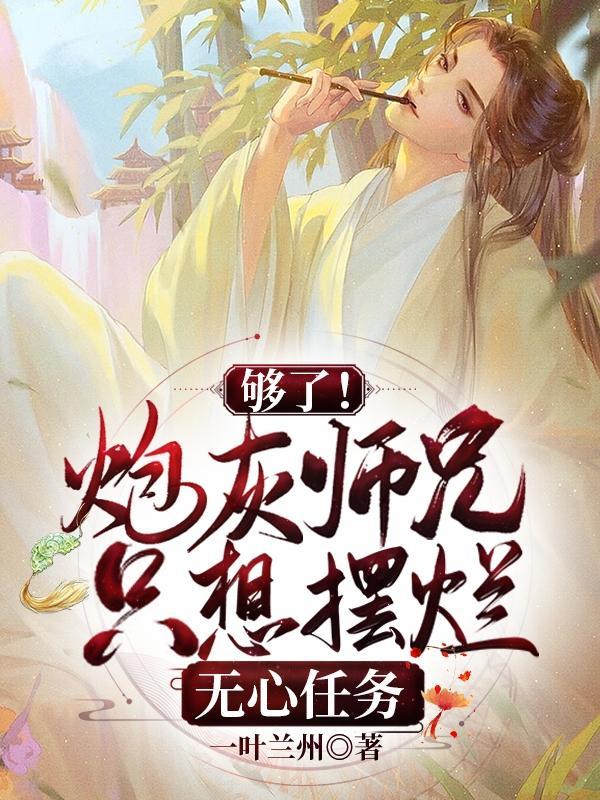富士小说>第7号无名档案百科 > 58 组织(第1页)
58 组织(第1页)
58组织
一九四八年的夏天在一道道无声的炮火之中悄然到来。前线早已打得不可开交,後方的人们在真假难辨的新闻报道和日复一日飞涨的物价中惶惶度日。内战已经打了两年,没有人知道这一场战争何时结束。徐应明在一个闷热难耐的清晨收到了朱砚平的来信。在看见信封上那一行熟悉的字迹时,她竟有一瞬间的怔愣。信是从沈阳寄来的。徐应明心情复杂地拆开信封,目光匆匆扫过。 徐应明中校亲啓:自南京一别,已逾一载。昨日傍晚时分,于沈阳城内侦察巡视,不知觉间竟行至徐家老宅。见庭前草木萋萋,思及眼下战局,不禁触目伤怀。又想到从前你在这里长大,漂泊十六载竟不得归,不住扼腕叹息。去年八月,杜司令调离指挥部,陈丶卫二人先後接替其职。然而不曾想共军来势汹汹,我数百万军队竟然节节败退,近百平方公里土地拱手相让,如今惟馀长春丶沈阳丶锦州丶葫芦岛等几座孤城矣!卫司令命我随军驻守沈阳,然眼下形势却不知又能撑得几日。沈丶长交通断绝,单凭空运补给已无法维持。困于城中,一连数日只闻城外炮火连连,电台信号时常中断。又悉得城外共军指挥竟是你的老朋友周先礼。听闻此人当年离沪赴渝期间,曾于延安“抗大”进行为期数月的军事培训。如今看来,其用兵谋略同军事眼光确非寻常人。周同你相交不浅,每每思及此,都不住感叹,若是当初毛人凤不曾将你派去杭州,或许在这里,我们同共军还有得一丝谈判的馀地。前路未明,心绪黯然,就此搁笔。望安。民国三十七年七月四日朱砚平末尾还有一行小字——另,前些日子已吩咐陈副官,遵照校级军官军属待遇,着人修缮令堂之墓,特此相告。徐应明看着信纸上的文字,忍不住心想,这倒是朱砚平难得的吐露心声。杜聿明调离东北,继任的陈诚本就同军统一系不合,自是对朱砚平处处刁难。官场失意,加上对眼下局势的无能为力,竟也让朱砚平这个老狐狸生出了倾诉的欲望,言语之间也多了几分真诚。徐应明轻叹一声,摇摇头,将信纸装回信封,然後…
一九四八年的夏天在一道道无声的炮火之中悄然到来。前线早已打得不可开交,後方的人们在真假难辨的新闻报道和日复一日飞涨的物价中惶惶度日。
内战已经打了两年,没有人知道这一场战争何时结束。
徐应明在一个闷热难耐的清晨收到了朱砚平的来信。在看见信封上那一行熟悉的字迹时,她竟有一瞬间的怔愣。
信是从沈阳寄来的。徐应明心情复杂地拆开信封,目光匆匆扫过。 徐应明中校亲啓:
自南京一别,已逾一载。昨日傍晚时分,于沈阳城内侦察巡视,不知觉间竟行至徐家老宅。见庭前草木萋萋,思及眼下战局,不禁触目伤怀。又想到从前你在这里长大,漂泊十六载竟不得归,不住扼腕叹息。
去年八月,杜司令调离指挥部,陈丶卫二人先後接替其职。然而不曾想共军来势汹汹,我数百万军队竟然节节败退,近百平方公里土地拱手相让,如今惟馀长春丶沈阳丶锦州丶葫芦岛等几座孤城矣!
卫司令命我随军驻守沈阳,然眼下形势却不知又能撑得几日。沈丶长交通断绝,单凭空运补给已无法维持。困于城中,一连数日只闻城外炮火连连,电台信号时常中断。
又悉得城外共军指挥竟是你的老朋友周先礼。听闻此人当年离沪赴渝期间,曾于延安“抗大”进行为期数月的军事培训。如今看来,其用兵谋略同军事眼光确非寻常人。
周同你相交不浅,每每思及此,都不住感叹,若是当初毛人凤不曾将你派去杭州,或许在这里,我们同共军还有得一丝谈判的馀地。
前路未明,心绪黯然,就此搁笔。
望安。
民国三十七年七月四日朱砚平
末尾还有一行小字——
另,前些日子已吩咐陈副官,遵照校级军官军属待遇,着人修缮令堂之墓,特此相告。
徐应明看着信纸上的文字,忍不住心想,这倒是朱砚平难得的吐露心声。
杜聿明调离东北,继任的陈诚本就同军统一系不合,自是对朱砚平处处刁难。官场失意,加上对眼下局势的无能为力,竟也让朱砚平这个老狐狸生出了倾诉的欲望,言语之间也多了几分真诚。
徐应明轻叹一声,摇摇头,将信纸装回信封,然後随手丢进抽屉里。
杨秘书敲门走进来,神色严肃。
“专员,总部发来的绝密电报。”
徐应明应了一声,接过电报纸,从上锁的柜子里取出和总部联络的电码本,逐字翻译。
是谭主任发给她的密电。电文里说,莫晓南即将被共産党方面派来浙东根据地,要徐应明想办法和她接上头,并从她的手中拿到共军在济南的军事作战图。
徐应明的眉头渐渐扭作一团。
杨秘书见状,不解地问:“专员,怎麽了?”
徐应明将电报纸对折叠好,哗的一下擦亮火柴,将电文销毁,然後站起身披上外衣,吩咐杨秘书:“我出去一趟,你在这儿守着,有事情回来跟我汇报。”
杨秘书应下,知道这份密电怕是事关重大,不再多言。
徐应明没有惊动汽车大队的司机,而是招手叫了一辆黄包车,然後晃晃悠悠地来到报社,按照约定在《中央日报》上刊登了一份寻人啓事。
她将写好的纸条内容递给工作人员,道了声谢,转身的时候与一戴着宽檐礼帽的长衫男子擦肩而过。
徐应明在经过的那一瞬间,忽然觉得那人有些许熟悉,在几步之外停下来,回头看去,那人却毫无反应一般同报社的工作人员说着话。徐应明确信那声音自己从未听过,不禁微微皱眉。
她想要上前一探究竟,却又忽然想起来,自己从保密局出来时并未掩饰,只怕自己前脚刚踏出院子,消息後脚便传到了孟均漱的耳朵里。
如果真的是组织的人,她便更不能上前。
徐应明抿了抿嘴,收回目光,大步向报社外面走去。
三年了。
他们终于想起自己了吗?
徐应明茫然地走在大街上,目光有些涣散。她只觉得自己的心口跳得厉害,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委屈涌上心头,她微微仰起头,眨眨眼,可实际上眼中却干涩得没有半点湿润。
大街上的行人相较于前两年已经少了许多。政府不遗馀力地宣传着远方战事的胜利,可另一边,高官富商们却争相兑换着黄金,物价飞涨,法币贬值,整座城市虽远离战火,却早已是人心惶惶。
徐应明的内心并不比这些杭州城中的人们轻松。
断联,静默,唤醒信号,再一次断联……还有日复一日地审阅着浙江站一份份针对组织的工作汇报。
所有的这些都重重地压在自己的神经上,令她时常感到喘不过气来,然後便是一阵恍惚,仿佛七年前的那个傍晚,自己不曾走进过烟杂店,“信天翁”这个代号也不曾出现过。
一年前西湖边上的那一次联络仍旧历历在目。
希望过後,便是更大的失望。
她害怕这一次,又是一场空。
徐应明辗转整夜不曾入眠,直到第二天一早,当她在《中央日报》上自己那一则寻人啓事背面的“读者来信”板块,看见了久违的联络暗语时,她终于长叹了一口气。
简单收拾後,徐应明便撑着伞,一身素色旗袍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