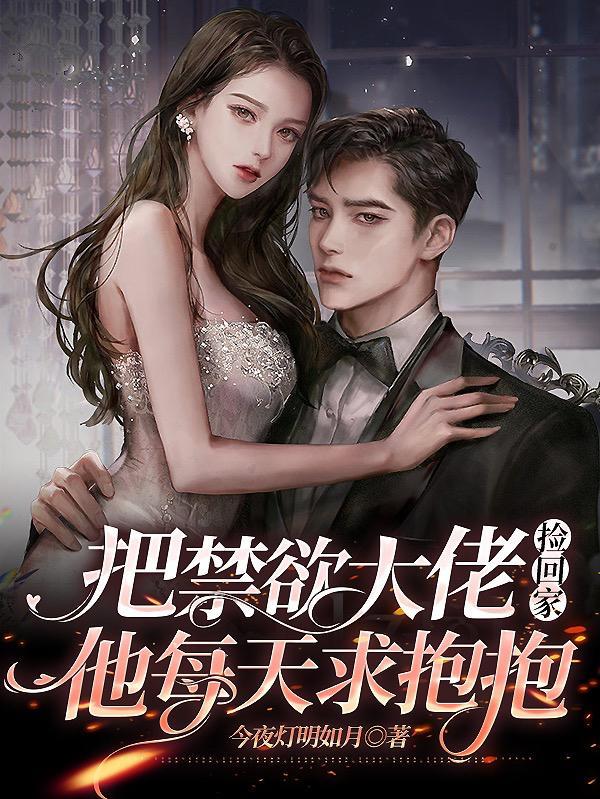富士小说>spring是什么意思 > 第 43 章(第2页)
第 43 章(第2页)
最终,我选定了一个最简单的丶由几个电阻电容构成的无源电路。它産生的噪音相对稳定,频谱特征也较为清晰。我将实时采集的噪音数据,映射到一台高流明投影仪上,投射在工作室一面空白的墙壁上。
关掉所有灯。
黑暗中,只有墙壁上那片随着无形电流微微脉动丶变幻的光影。它不像任何具体的形象,只是一片不断生成丶消散的抽象场域。但如果你凝视得足够久,仿佛能“看到”电流的流淌,“听到”电子的窃窃私语。
它不再是我“创造”的图像,而是某个物理系统自身状态的丶实时的丶视觉化的“显形”。
我将其命名为:《场域I-电路》。
我邀请王锐来看。他站在黑暗里,盯着那片光影看了很久,然後转向我,眼神发亮:“这是……将系统的熵增过程可视化了!太有意思了!你有没有试过改变电路的温度?或者施加外部电磁场?看看图谱会怎麽变化?”
他的反应完全在科学的频道上,却恰恰点出了这个作品的核心——它关乎过程,关乎系统对环境的响应,而非一个静止的结果。
我也给陈洄发了视频。她看完後,沉默了片刻,说:“粗糙,但方向对了。比模拟更接近本质。可以考虑引入反馈机制,让图像的变化反过来影响电路本身,形成闭环。”
她的建议再次将我推向更深的层次。
《场域I》完成後,我没有公开展示的计划。它更像一个原型,一个概念验证。但它对我而言,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我从“塑造物质”转向了“介入系统”,从追求最终的“物体”转向了呈现持续的“过程”。
就在我沉浸于这种新探索时,林助理带来一个消息。之前寄送DNA胸针的那家神秘画廊,终于有了回音——不是通过邮件或电话,而是寄来了一份纸质邀请函。
邀请函设计极简,纯黑色卡纸,上面只用烫银字体印着几句话:
「诚邀张宸之先生
参与‘编码解码:後生物时代的艺术叙事’国际艺术家驻留项目
地点:冰岛,雷克雅未克
时间:三个月」
落款是那个画廊的名字,以及一个冰岛极光研究机构的LOGO。
冰岛。极光。後生物时代。
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像一把钥匙,精准地插入了我当前思考的锁孔。
冰岛,那片拥有极端自然环境和独特地磁活动的土地,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丶充满原始“语法”的场域。极光,则是太阳风与地球磁场相互作用産生的丶最壮观的动态显形。而後生物时代……正与我近期对生命丶信息丶技术的思考紧密相关。
这封邀请函,不再像一次偶然的投石问路,更像一次经过精密计算的丶量身定制的召唤。
我看着邀请函,又看了看工作墙上那片依旧在无声脉动着的《场域I》的光影。
下一个“场域”,似乎在遥远的北极圈内,等待着我的介入。
而这一次,我将面对的,不再是工作室里的小小电路,而是整个星球,乃至太阳系范围的,宏大语法。
我拿起笔,在邀请函的回执上,缓缓画下了一个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