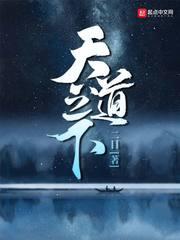富士小说>spring festival > 笔记(第1页)
笔记(第1页)
笔记
河水在脚下奔流,裹挟着上游的泥沙和断枝,发出沉闷而持续的呜咽。
那束偶然漏下的阳光很快被移动的云层吞没,天色复又归于一种均匀的丶哀戚的灰。但邱霭明那句“能画出来,就好”,像一枚小小的楔子,钉进了我冰封的情绪里,裂开一道细不可见的纹。
我们最终没去找地方热包子。
邱霭明把我带到河堤下一处废弃的小亭子,石板桌椅冰凉,但总算能避一避又开始飘洒的雨丝。
他变戏法似的又从那个大口袋里掏出两个保温杯,拧开一个,递给我。是滚烫的姜茶,辛辣的甜味混着姜的暖意,瞬间从喉咙一路烧进空瘪的胃袋,驱散了些许浸入骨髓的寒意。
我啃着冷掉的包子,面粉已经有些发硬,馅料也凝出油块。但咀嚼这个简单的动作,吞咽这个生理需求,让我重新感觉到自己还活着,还是一个需要进食的丶物理意义上的存在。
“命运啊……”我盯着亭子外被雨点击打出无数涟漪的河面,声音干涩地开口,“他不声不响的走了,我好不甘心”
邱霭明捧着另一个保温杯,没有看我,只是嗯了一声,示意他在听。
“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个‘神明’。就像一到惊鸿,永远在那里,安静,温和,甚至有点模糊,我好像从未主动的了解他。
我从没想过,我会有‘不甘心’这种东西。”我试图描述那种颠覆性的感觉,词汇却贫乏得可怜,“那感觉……就像你一直以为自己在临摹一幅静物画,画了十年,突然发现画布背面,用你看不见的颜料,画着完全不同的丶汹涌的东西。”
邱霭明沉默地喝了一口姜茶。雨声淅沥,填补着我们之间的空白。
“小禹以前想学文学。”他突然说,声音平静,“不是搞解析那种。是想做作家。他跟小洄提过一次,小洄说……就是他发小陈洄,不怎麽支持。他很小就没了家人,许多事特别仰仗这个姐姐”
我顿了顿,看着亭外绵密的雨丝。
“後来他选了金融。直到他去年走了,整理东西时,我才在他箱子最底下,发现一本快烂了的书,还有几块他偷偷抄下的,很美的句子。怪我当时不在,没好好问他……”
他没再说下去。也不需要再说。
一种沉重的默契在我们之间弥漫开来。原来不止周禹,或许许许多多的人,都曾悄悄地把那个真正的自己,那个有着微小梦想和“不甘心”的自己,藏进了生活这幅巨大画布的背面,最终被时光的尘埃覆盖。
包子吃完了,姜茶也见了底。身体暖和了些,但心里的那个洞,依然空落落地透着风。
那不仅仅是对失去爱人的悲痛,更混杂着一种迟来的丶无法弥补的歉疚——对我从未试图去了解画布背面的那个他,而感到的歉疚。
“回去吧。”邱霭明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你的画还没干。”
我们沿着来路往回走。雨比来时大了一些,敲打着伞面,噼啪作响。
经过街角那家老旧的杂货店时,我忽然停了下来。
橱窗里摆着各种零碎东西。针头线脑,搪瓷缸子,廉价的塑料发卡。
角落里,摆着一排那种小学生用的丶塑料壳的日记本,封面印着过时的卡通图案。
鬼使神差地,我推门走了进去。店里有一股陈年的糖果和灰尘混合的气味。一个戴着老花镜的店主从报纸後擡起头,看了我们一眼。
我走到那排日记本前。颜色俗气,质地粗糙。和周禹枕下那本,几乎一模一样。
我伸出手,指尖拂过那些光滑又廉价的塑料封皮。
想象着几年前,或许也是在一个这样的雨天,一个年轻的少年,怀着隐秘的心事,走进一家类似的杂货店。
他是个孤儿,没有了亲人,只能靠补偿金与奖学金度日。
“要这个吗?”店主问。
我回过神,指了指其中一本蓝色封面的,上面印着一艘歪歪扭扭的帆船。
付了钱,我把那本轻飘飘的丶毫无分量的日记本揣进外套口袋里。它贴着我的胸口,像一个无声的承诺,一个过于迟到的回应。
回到画室。那幅画还在画架上,颜料未干,那片混沌的灰黑和那一点微弱的黄光,在阴雨天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更加压抑,也更加真实。
我没有再去动笔。我只是搬了把椅子,坐在它对面,静静地看。
邱霭明说得对。能画出来,就好。
我不是在画他。我是在尝试读懂他。用我的方式,用颜料和线条,去触碰那个被自认我忽略了多年的丶画布背後的灵魂。
窗外的雨声不知何时停了。屋子里很静,只有我和画布对视着。
那一刻,我清晰地感觉到,悲伤的形状改变了。
它不再是一片无处着力的丶弥漫的虚空,而是变成了手里这本廉价日记本的确切重量,变成了画布上那片需要我去一层层解读的丶浓稠的色彩。
痛苦依然在,并且可能永远都在。但它开始有了纹理,有了色彩,有了可以落笔的地方。
周禹不在了。但我和他之间,那场迟到了多年的对话,似乎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