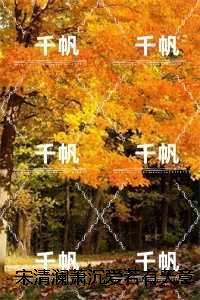富士小说>悔弃明珠越山雀 > 第34章 她的小狗完(第7页)
第34章 她的小狗完(第7页)
小狗想了想,眯着眼睛笑了,他小声道:“好吧,那你要记住了,我要最好的名字!”
夜色中,谁也看不清虞惊霜的脸,她缓慢又坚定的点头,在心中默念:好,我答应你。
又过了很久,小狗的声音突然响起:“霜,你知道吗?”
他慢慢道:“如果能回到那一天,我也还是会给你挡刀的。”
“我从来不后悔。”
……
那一夜后,小狗背上的伤口慢慢好转,然而,他体内的毒却越来越霸道地侵蚀着内里。
他的意识也慢慢模糊,整日昏睡,清醒着的时候越来越短。
直到有一天,他难得清醒,央求医者给他看看背上的伤,抚摸着那道伤疤,他迷惑而难过地问:“为什么明明看起来已经快好了,我却还病着呢?”
医者守在一旁,不敢多说一个字。
虞惊霜耳提面命,强令他们所有人都对小狗守口如瓶,可不用说都知道——小狗活不成了。
小狗放回铜镜,无意中在镜中看到了自己的脸,他动作一顿,沉默了。
等傍晚虞惊霜来看他的时候,就发现他侧躺背对着她,脸上还蒙了一块不知哪里来的黑纱。
虞惊霜不解,她问:“怎么了,小狗?”
他没有转身,还捂住了自己的脸,一言不发。
虞惊霜担心他闷到自己,刚上前,就听到小狗瓮声瓮气的声音传来:“我真的好丑。”
他慢慢放下了手,露出来的面庞上,有着一道道纵横交错的黑纹,轻微地鼓胀着,触目惊心,仿佛他的脸下一瞬就要自黑纹处裂开。
他的眼泪无声无息地落了下来:“为什么要现在才让我想起来,这是一张很丑、很可怕的脸?”
他慢慢复苏着的记忆,没有告诉他关于自己的往事,却只让他找回了自己的言语和情感,在他毁了容的情况下,才赋予他识别美丑的意识。
虞惊霜心中如被恶狠狠一敲,她忍着哽咽,蹲下身慢慢去抚摸小狗的脸,她说:
“因为是你,所以一点也不丑、不可怕。因为你是……我的最惹人怜爱的小狗。”
他躺在床榻上,静静地仰望着虞惊霜,艰难地伸手,为她擦去了泪珠:“好。”
他的目光如第一次相见那般,充满天真的信赖:“霜说什么,我都相信你。我一点也不丑、也不可怕。”
自脸颊上出现黑纹后,仿佛昭示着死亡的阴影缓缓盘旋降临,小狗再也没有意识清醒的时候。
医者还在为他每日熬药、煮药,喂他喝下一幅幅不同的汤药。
虞惊霜总是静静地守在一旁,轻声念他的名字:小狗、小狗。
快点醒过来。
然而,一天天过去,他的手脚处也弥漫上了黑纹,甚至开始鼓胀、裂开、流脓。他在病中疼的皱眉流泪,可仍然不肯睁开眼睛。
到后来,连晾晒在外的马肉干都发了霉,小狗仍固执地昏睡着。
一日傍晚,虞惊霜处理掉那些发霉的马肉干,回营帐的途中,两个士兵在与医者闲聊。
医者低声道:“就这几天了,真的活不成了……那毒太奇异霸道了,我都闻所未闻,啧……可怜啊,这么一天天拖着,走的时候也痛苦。”
虞惊霜站在几人背后,那话传入耳中,不知为何,她的心竟然异常的平静。
其实对于这个结果,她早已有所预料,只是一直都在掩耳盗铃罢了。
她不知自己是如何走回了营帐中,床榻上的小狗呼吸已然非常微弱,气若游丝。
虞惊霜蹲下身来,有一搭没一搭地抚摸着小狗的头发,神思慢慢飘远。
这时候,突然,她手下的脑袋微微一动,虞惊霜一怔,她垂眸,正对上小狗慢慢睁开的眼睛。
那双原本棕金色的眼眸已经蒙上了一层灰翳,雾蒙蒙看不清眼中神采,虞惊霜定定看着他,心底一片柔软。
她闭了闭双眼,再睁开,已经坚定了心中所想。
她俯下身靠近小狗耳边,像诉说一个秘密一般,轻声道:“我带你走吧,小狗。”
她沉静地自马厩牵了一匹马过来,将小狗扶上马背,自己也翻身上去,小野狗崽在脚边急切地转来转去,虞惊霜低头看了它一眼,也一并将它揣在了怀中。
她策马一直向着西边走去。
越过小狗曾采摘花朵的山坡。
越过两人一起捡拾过木柴的坑洼。
越过遍地晶莹碎石子的原野——
直到耳旁的山风带来了水波澎湃的声音,眼前浮现出一条宽阔汹涌的长河,她才拉住了缰绳。
春光作序,万物和鸣。
山风吹满原野,吹落了不知名的淡蓝花瓣如锦绣铺地。
虞惊霜扶着小狗寻了一块巨大的岩石坐下,为他围上了大氅,柔软的皮毛拂过他的嘴唇,像一个吻轻轻落下。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 宋清澜萧沉爱若有天意,兜转终可回:结局+番外宋清澜萧沉
- 原来当年出卖父亲的人竟然不是陆风,而是为父亲讨回公道的萧沉。那具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