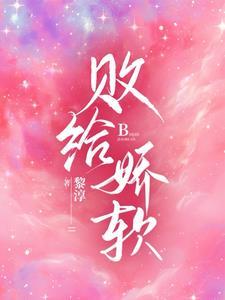富士小说>团宠锦鲤被重生首辅拐跑啦免费阅读 > 第130章(第1页)
第130章(第1页)
一筐梨子便是两个铜板,快的一天削个十来筐都不成问题。
只是这活儿也不好做,比较费手,手臂容易酸,手指头因为长时间接触梨子水而被泡软,泡脱皮的也有,削着削着就慢了,不仅耽误了工期,卫生问题也无法保证。
李常林一天三餐都是在林家吃的,这一日晚饭,便顺口提了一嘴儿,说削梨子皮太费手了,一个人削两天就吵着说削不动了,手也废了,削出来的梨子卫生也无法得到保障,目前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林大力这些时日都忙着给李常林修房子的事儿,听到这话,心思就转开了,当晚便琢磨了一样工具出来。
有了这个工具,不仅削梨子的速度提升很多,而且不需要工人的手直接接触梨子,卫生也得到了保证。
那是一个木制的架子,拿在手上小巧轻便,将野山梨子放在架子中的凹槽内,在将架子的另一半扣在梨子上,接着往下一拉,梨子皮就被削开了,落出来白嫩嫩的梨肉。
“哇……竟然还有这样的工具?”李常林惊得不行,这工具看似简单,原理也简单,类似乎木工的刨子,但谁能为了削梨子而发明这么一套工具呢。
“能用不?”林大力问。
“太能了,大力哥,你真厉害。”李常林与林正和同年,所以此时称呼李大力一声大力哥倒是正常。
林大力却颇有些不自在,不敢相信李常林这样的贵公子竟然与自己称兄道弟,红着脸呐呐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大力哥,能多做一些不?”李常林问。
林大力点头:“自然是可以,我让师父帮我做,明日就能做出来五十个。”
李常林当即表示,以一个工具五十个铜板的价格订制一批。
如此一来,工人们的效率就提高很多。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梨子都需要去皮去籽,只是他们如今制作的这一批秋梨膏是销往京城的,价格不菲,各方面自然比较讲究一些。
李家为了打开京城的销路,早在收到张启风来信的时候,便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专门售卖一应产品的店铺,如今已经进入宣传阶段,就等这第一批秋梨膏上市了。
野山梨子酸涩硬实,削了皮再去籽,是为了去掉秋梨膏的涩感,让秋梨膏口感更好。
除了售价较高的这一批秋梨膏,往后还会制作售价相对便宜的,便是整个野山梨子直接熬制,不需要耗费那么多人工,口感虽然没那么好,但功效是一样的,价格也比较亲民,普通百姓也买得起。
秋梨膏开始熬制之后,方小小接连三天都蹲守在作坊内,就是为了保证秋梨膏能达到自己想要的口感。
除了纯粹的秋梨膏,还有加了川贝,蛇胆等物的秋梨膏,用于小儿止咳有特别好的效果。
小孩儿生病可不会像大人一样,想着赶紧把药喝了便能好,他们闻着药汤的苦涩味儿,再看那黑不溜秋的药汁,那是打死都不喝啊。
方小小喝了那么多年的汤药,自然知道药有多苦,但为了活命,苦也不得不喝。
如果能有好喝的药,那岂不是很幸福?被汤药折磨多年,她知道喝药有多痛苦,所以在药膳的口感上,她和张启风的追求是一个等级的。
一定要好喝。
如何把药用秋梨膏熬好喝,便是一个大问题,好在方小小有经验,很快便熬出来了。
给林大胖他们试了一下,这一群小屁孩儿都纷纷表示:想生病,想喝秋梨膏。
李常林尝过她熬的秋梨膏之后,整个人都愣住了……
京城有方小小的传说
“梨香浓郁,入口清甜,这哪儿是秋梨膏啊,这是梨子汁吧?小小,你莫要骗我啊,这不是梨子汁么?每到夏日,府里每个主子隔日便有梨子汁用,就是这个味儿,但是你这秋梨膏更好喝,清甜不腻,也没有酸涩味儿,太好喝了。”
李常林惊为天人。
这就是太医院院正的实力么?怪不得宫中的太后娘娘一直对张启风的药膳念念不忘。
当那些口味各异,但都一样难喝的药变成了一种美味儿,谁不上头?
这是纯秋梨膏的味道,比梨子汁都要好喝。
而加了川贝,蛇胆的秋梨膏,则多了点淡淡的药草香,混合着梨子的香甜,两种味道奇异的融合在一起,竟相辅相成,成了一种全新的美味儿,一样好喝。
方小小自己兑水喝了一大碗,也十分满意。
几乎与师父熬出来的秋梨膏无异了。
“可以了,便按照我的步骤来,时间,火候,分毫都不能差。”她交代负责其中细节的一应工人。
熬制秋梨膏的作坊里分工十分明确,有负责生火看灶的,有负责榨梨子汁的,有负责搅拌梨子水的,方小小将自己的要求与工人们一一细说,以确保每个步骤都万无一失。
“一旦有一个步骤出现差错,秋梨膏的口感就无法保证,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打起精神来,不能出错,如果出了差错,要及时禀告,不可一错再错,加重损失。”
方小小说话软和,李常林却不一样了。
身为世家少爷,身上自带着一股威势,方小小将要求与工人们说了一遍之后,他又强调了一次,让人不敢轻忽。
忙碌了大半个月,第一批秋梨膏终于装进了船舱,走水路运往京城。
从秋梨膏的包装上就可以看出李家对此次合作的重视。
竟然用的是属地的白玉瓷瓶,一瓶可装八两重的秋梨膏。
这瓷瓶质地轻薄,烧制出来之后有玉石的质感,举国闻名的雨花酿,用的便是这种白玉瓷瓶,据说将秋梨膏盛放在白玉瓷瓶内,可以久放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