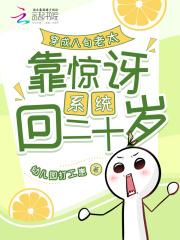富士小说>一寸光阴一寸心是哪首歌的歌词 > 为敌贼寇露绝技 欲助官人窃密文(第2页)
为敌贼寇露绝技 欲助官人窃密文(第2页)
吴立人于贡院左近挑了一间名为“思无涯”的客栈。“思无涯”三字取自孟郊的名诗《登第後》,其後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至今广为传颂。客栈以此三字为名,既有科举登第的好彩头,又有客居思乡情切之意,还有别于其它什麽“状元楼”“状元古寓”的直白,显得妙趣横生。
因距科考还有些时日,吴立人不单在客栈温书备考,也常与士子结社交游丶饮酒吟诗,屡屡回来时酩酊大醉,或是打包一些吃食,“这会仙楼正店的菜品是极贵的”;或是喜不自禁仍面有得色,“今日得某某大儒青眼有加”。偶尔烦闷时也会带小月去汴梁的夜市逛逛,曹婆婆的肉饼丶史家的瓠羹丶万家的馒头丶王道人的蜜煎……都让小月流连忘返。
眼见大比之期临近,一日吴立人外出而回,闷闷不乐。
“官人,可是遇到忧心之事?”
“坊间盛传,拗相公复起,本次策论会与新法有关。但又有传言说,此次拗相公虽然复起,但太皇太後丶皇太後以及一干重臣都是竭力反对。再加上前些日子彗星凌月,司天监奏曰:‘百姓怨气凝聚于地,祖宗积愤上彻于天,故彗星见,乃大灾之兆。’听说官家又有罢相之议。所以策论该如何应对,我还未决定。”
“官人不提,妾身也想告之官人,妾身午间欲去为官人添置一些笔墨,途径一家书店,见有两人神色尴尬。”
吴立人也来了兴趣,“怎生尴尬?”
“一儒生打扮的年轻人同一鹰鼻鹞眼仆人打扮的中年汉子相谈甚密。期间儒生刚问出‘此科’字样,那仆人连忙让其噤声。然後四处张望一番,拉着儒生便走。”
“一个读圣贤书的士子,怎能与一下人相交甚密,更何况此等时节,定有不可告人之密。”
“妾身也有此疑问,故一路尾随。後来二人行至樊楼,妾身记得官人曾说,这樊楼是汴梁七十二家正店之首,这可不是一个杂役能去得起的地方,所以更觉有蹊跷。妾身也充作食客进去,发现书生二人要了一最僻静的单间。妾身在其旁边的房间内点了几样吃食以作掩饰,听得那士子二人谈话果与此次科考有关。”
“娘子速速说来。”
“妾身听得一个粗粝的声音说:‘此科策论,定要突出新法的迫在眉睫,或为变法摇旗呐喊;或援古据经,指出施行变法实为效法先王,有典有据;或以史为鉴,指出推行新法必要百折不挠,逆水行舟。但唯一点却需注意,行文总要含蓄不可太过直白,不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是为变法而写。这是宫里官家身边的中官传出来的确信。’”
吴立人听完一边低头思索一边自言自语,“既要支持,还不要坦言。这是说官家心向新法,只是迫于内外压力,不敢过于明显!我懂了,这个说法颇为贴近真实。而且这段话语显然不是一个杂役能道出的,应该是转述某位中官的原话。”
想到这里吴立人擡头看向小月,“娘子你可是居功甚伟啊!”但随即他又开始沉吟,“只是即使知道了官家的心思,这篇策论也不好着笔啊。而且也不知更具体……”
“官人,妾身还听他们说题目……”
“嘘!”吴立人连忙止住小月,打开房门四周环顾,见四下无人才关上门,让小月附在耳边告知细微。
见吴立人听得具体後,仍愁眉不解。小月犹豫了片刻,又说道:“妾身还在书店看见一本集子,不知对官人是否有臂助。”
“哦,你先放那儿,容我再思索一番。”
“官人,中午樊楼的吃食,妾身未敢一人独享,这就去吩咐店家热了来。”
“哦,好。”吴立人仍在构思。
纵使一桌珍馐美味,吴立人依然味同嚼蜡,直至小月收拾完桌子,他仍低头沉思。
忽一阵风起,熄了蜡烛。待小月重新掌上灯,只见刚才留在桌上的小册子被风卷开扉页,露出内里清秀的小楷,“盘庚之迁咨胥皆怨民谤汹汹度义而动南渡涉河定都为亳百姓由宁殷道复兴”。
吴立人顿时来了精神,这是商王盘庚迁都的典故。盘庚因旧都奄地多水患,打算迁都,百姓不愿迁徙之苦怨声载道。盘庚分别加以劝谕警告,最终南渡黄河,迁都于亳州。百姓们渐渐安定,殷朝的国势又一次兴盛。以此典故顺应介甫相公的“天变不足畏丶祖宗不足法丶人言不足恤”实是恰如其分丶得其所哉。
再往下看,这篇文章不仅有关于“民怨”的反驳,还针对旧党诘难的“侵官丶生事丶征利丶拒谏”等一一作出解释。更难能可贵的是文中旁征博引丶借古喻今只指明了“是”,却并未言“非”,显得风格高洁且含而不露。整篇文章虽不说字字珠玑,但也文辞华丽丶花团锦簇,一以贯之的娟秀小楷更是让人赏心悦目当是手抄本。只是这小册子的封面并未有题名,不知为谁所作。
“娘子这册子从何而来?”
“妾身在书店听那二人谈话时,假借翻阅此册子。虽不解其意丶但觉那笔字写得可人,就买来了。”
“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啊!”吴立人喜不自胜。连带着小月也喜上眉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