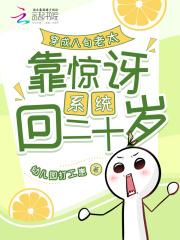富士小说>林山深处有人家是什么诗 > 第14章(第1页)
第14章(第1页)
而自己呢?刚才对着何虞欣发的火,却撒在了他身上。
“刚才……”洛林远张了张嘴,想说“对不起”,可那三个字堵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口。他活了二十八年,骄傲了二十八年,除了对着钢琴,从没对谁低过头。
最终,他只是松开晏逐水的手,把医药箱推回抽屉里,别开脸:“地上的水……等会儿拖了。”
晏逐水点头,知道他这是松口了。他站起身,想往客厅走,却被洛林远又叫住了。
“晏逐水。”
这是洛林远第一次连名带姓叫他。
晏逐水回头看他。
洛林远看着他,眼神复杂,好像有很多话想说,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低声说:“评委的事……我不去。”
晏逐水愣了愣,随即明白了——他是在跟自己解释。解释他没听何虞欣的话,解释他不会离开。
晏逐水的嘴角忍不住往上扬了扬。他没说话,只是对着洛林远,轻轻点了点头,眼神亮得像落了星星。
洛林远看着他的眼睛,心里那点别扭忽然就散了。他别开脸,假装整理书桌上的文件,嘴角却悄悄勾了下——很轻,像风吹过水面,漾开一圈极淡的涟漪。
客厅里的水渍还没拖,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落在地板上,亮得发暖。厨房的方向传来拖把拖地的声音,一下一下,很轻,很稳,像首安静的歌。
洛林远靠在书桌边,听着那声音,忽然觉得——好像这样也不错。
有个人在身边,哪怕是个哑巴,哪怕只是拖地的声音,也好过对着满屋子的冷寂,对着那扇锁死的琴房门,独自舔舐伤口。
只是他没看见,厨房门口,晏逐水握着拖把的手,轻轻抖了一下。指尖的创可贴蹭着拖把杆,有点痒,有点暖,像刚才洛林远低头给他贴创可贴时,落在他手背上的、那缕极轻的呼吸。
无声的乐章与窥见的秘密
晏逐水发现那摞乐谱时,是个晴好的午后。
洛林远去医院复诊了,临走前嘱咐他把书房的书架再擦一遍——上周何虞欣来过后,洛林远就没怎么进过书房,书架上落了层薄灰,像蒙着层心事。
阳光透过百叶窗斜切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道亮纹,空气中的尘埃在光柱里跳舞。晏逐水踩着梯子擦顶层的书,指尖刚碰到一本精装的《巴赫平均律》,就听见“哗啦”一声——书架最里层的一摞乐谱没放稳,顺着书脊滑了下来,散落在地毯上。
他连忙从梯子上下来,蹲身去捡。乐谱大多是打印的,纸页边缘已经卷了边,显然被翻看过很多次。可当他捡起最底下那本时,指尖顿住了。
那是本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边角磨得发白,封面上没有字,只在右下角画了个小小的高音谱号,墨迹已经褪色。晏逐水认得这个记号——以前在洛林远的演奏会海报上见过,是他的专属标记。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翻开了封面。
第一页是工整的乐谱,铅笔写的,音符排列得像列队的士兵,旁边用红笔标注着“强弱”“换气”“速度稍快”,是《月光奏鸣曲》的改编片段——和那天他在音响里听到的版本几乎一样,只是这里的转音处理更细腻,像藏着串没说出口的话。
晏逐水的心跳慢了半拍。他指尖轻轻拂过纸页,能摸到铅笔划过的凹痕,能想象出洛林远伏在灯下改谱的样子:眉头微蹙,指尖捏着铅笔,偶尔停下来敲敲桌面,眼里映着台灯的光。
他往下翻。后面的乐谱渐渐变得潦草。有的音符被划掉又重写,有的地方用钢笔泼了大片墨迹,像盛不下的情绪。到了笔记本中间,甚至没有完整的乐谱了——纸页上写满了零散的句子,字迹狂乱,有的字被圈了又圈,有的被划得看不清原貌:
“左手还是僵……到底要练多少遍?”
“今天试了试跳音,指尖发颤。他以前总说我跳音像踩在棉花上……”
“雨又下大了。琴房的窗没关,琴键会不会受潮?”
“她昨天发了消息,问我好不好。好什么?”
最后那句后面,有几滴深色的痕迹,晕开了纸页,是干涸的泪痕。
晏逐水的指尖攥得发白。他看懂了这些话里的痛——不是手伤的疼,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连呼吸都带着的钝痛。那些被划掉的音符,被圈住的字,都是洛林远没说出口的挣扎:他还想弹,还在等,却又被现实按在原地,连指尖的颤抖都成了奢望。
他翻到最后几页,纸页忽然变得干净起来。上面只抄了一首曲子,是手写的五线谱,没有标题,旋律却异常熟悉——晏逐水的呼吸骤然停了。
是《枯叶》。
一首极其冷门的钢琴小品,作者是位早逝的波兰作曲家,生前只发表过三首作品,《枯叶》是最不为人知的一首。晏逐水也是在老家县城的旧书市淘到一张破唱片时,才偶然听到的——曲子像深秋的风卷着落叶,簌簌地落,没有大悲,却透着种化不开的空茫,像极了此刻落在纸页上的阳光,亮得人心里发慌。
他没想到洛林远会抄这首曲子。纸页右下角有行小字,用钢笔写的,很轻:“20191026雨。终于弹顺了。她站在琴房门口,没说话。”
2019年10月——正是洛林远车祸前一个月。
“她”是谁?是何虞欣吗?晏逐水想起何虞欣那天看洛林远的眼神,想起笔记本里那些关于“离开者”的碎语,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了,闷闷的。
“你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