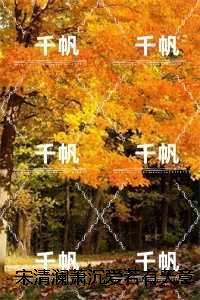富士小说>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画面 > 168 进退(第2页)
168 进退(第2页)
尉迟媱头发上的水,滴落池中,水声可闻:“需要我什麽?你做决定,和别人共进退的时候,甚至不会提前告诉我。”
尉迟媱把他从水中完全拖拽出来,衣服披到他肩上,又按住了他的颈链,换他一身惊颤:“如果你永远都不知道,生死之外,你也是我最重要的原则和底线,那我就永远不会需要你。我不会被自己的底线背叛第二次,自以为是的牺牲,把我救出地狱,但实际上,你的背叛,对我才是真正的地狱。”
尉迟媱松开手,漠然地说:“钟离未白,我从成年就戎马上阵,我眼里只有生死,我如果有事,你应该做好和我一起死的打算,而不是让我失去你,事情和你,你却永远比我分不出轻重。”
她转身出去,回到一样冷寂的将军府。
隔几日,钟离未白的病还没好,但尉迟媱已经准备回南方。
趁着今日难得有太阳,雪也化得差不多,她正在院子里磨刀。
浇些水在磨刀石上,她那双手,本来就和闺秀女子的不一样。
东方珀进来的时候,正好看到她两袖都扎在上面,露着与手背颜色有别的藕白手臂,上面有颜色更浅的旧伤。
“偃月刀就那麽重要?那帮涂梁人,能把你那刀当好刀吗?掉进别人的地盘,三年无人打磨,估计都锈成锅底了。”
尉迟媱都懒得看他,回他只需要一句话:“我有东方琅的消息了。”
东方珀就静止在了日光里,笑慢慢淡掉了,问:“她在哪里?”
“涂梁。”
“你说谎!”
尉迟媱回头看他:“你怎麽知道我说谎?”
他说:“因为我知道她在楚矶。”
轮到尉迟媱笑了一下:“所以你只是不知道她在楚矶的哪里?”她眯一眯眼睛,“刚好我知道。”
“尉迟媱,你我是完全可以合作的,你想要什麽?爵位?将军府昔日的荣耀?还是隔壁那个深不可测的病人?都可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只要你站在我这一边,这些我都可以承诺。”
尉迟媱没回答他,反而转过身,又磨了几个来回的刀。
等刀刃彻底亮了,才兴致恹恹地回头看他一眼:“太子殿下,你真是搞错了,我要什麽,从来不需要别人给。”她哼一声,“而且皇家承诺,我尉迟家早就看透了。”
“但你本来也没得选,父皇最小的那个皇子,至今不识字,他是天生痴傻,我是太子,你没得选。”
尉迟媱说:“既然如此顺理成章,你又何必着急?”
他沉默半刻,说:“越早,越可以尽快接琅琅回来。”他定要站在权力顶峰,然後让整个晟誉,亲自迎回他们的长公主。
“不可能的。”尉迟媱放下了袖子,“权力之路,满是枯骨,或许之前你是为了东方琅,可是从你给九皇子下药的时候开始,你也已经变了,是九皇子成了一个傻皇子,你才终于当到了太子。”她眼中尽是笃定。
而东方珀,也并不惊慌。
唇角勾起,他说:“但你没有证据。”
刀放在案上,京都的风,吹动了她的鬓发:“你以为我是什麽讲道理的读书人吗?在我们兵家,此时此刻,我三步之内就能取你性命,这就是我们的道理,我不需要和你讲证据。”
她坐了下来,也倒了杯温度正好的茶,喝着说:“我们又怎麽不是知根知底?你动我,丞相不可能放过你,而我动你,有人真跟我计较的话,丞相宁愿改天换地。”
“你太狂了!”
“我能说到做到,这算什麽狂。”她笑了,云淡风轻。
东方珀忍耐地闭上了眼睛,所以一直在提防,佣兵之权与当朝宰辅,一旦结合,这就是对皇位的架空。
圣上对此谨慎了一生,可事到如今,已经没办法了。
“东方珀,你是否疑惑过,早年你比东方珩,大皇子,好像也没有差多少,可是圣上偏偏不喜欢你?”
他沉默不语。
“你有楚矶血脉,这是原罪,圣上对你,就永远没有信任。我将军府也一样,圣上永远不会信任我。你也比我更清楚,太子之位只是稳住你的手段,所以你着急,因为你看不出来圣上的後手,你就需要我成为你的刀。”
东方珀就一直盯着她,忽然说:“但是,我信你。”
尉迟媱怔愣了一瞬。
“尉迟媱,我信你,母妃去世的前两年,我和琅琅无人问津,宫里嬷嬷都给我们吃馊饭,你发现了,你找那两个嬷嬷打架。”
他说:“父皇不信任将军府,是不相信将军府对皇位会没有兴趣,因为在你之前,都是男将军,有世俗眼光里,称帝的资格,他习惯了那麽提防兵家。可是我知道你,勾心斗角丶尔虞我诈的宫城之变,你根本没兴趣,战场丶自由丶傲视,这些才是你的兴趣,我可以满足你这种兴趣。”
他走近,也倒了一杯茶:“尉迟媱,如果以後是我做决定,我就可以给兵家自由,你只需对晟誉的国土负责,而不是对我负责,因为世俗眼光里,你这位女将军,永远无法称帝,不会引发民心动摇,而至于其他不世俗的眼光,我信任你,就说到做到,不怀疑,就是我的诚意。”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 宋清澜萧沉爱若有天意,兜转终可回:结局+番外宋清澜萧沉
- 原来当年出卖父亲的人竟然不是陆风,而是为父亲讨回公道的萧沉。那具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