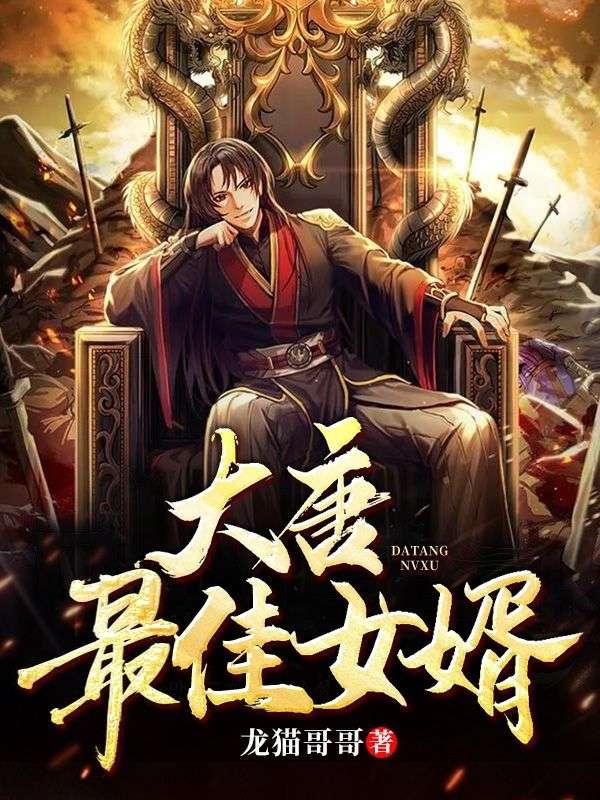富士小说>制霸一方是什么意思 > 第534章 一场跨城区的无声交响(第1页)
第534章 一场跨城区的无声交响(第1页)
回到家,赵工小心翼翼地将那包“文化保育补贴”的烟放在桌子上,然后走到储藏室,翻出了尘封多年的军鼓槌。
他拿着鼓槌,走到院子里,轻轻地敲击了三下。
鼓声在寂静的夜空中回荡着,带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节奏。
“老赵,练上了?”隔壁阳台探出一个脑袋,笑着问道。
“不是练,是回礼。”赵工笑了笑,抬起头,看着那轮明月,
就在这时,于佳佳的电话响了,看到来电显示,她的心跳不禁漏了一拍……
于佳佳看着屏幕上“陈工秘”三个字,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
电话那头传来公式化的女声,邀请她参加下周的“城市感知标准草案”闭门研讨会,说是领导特别指示。
于佳佳听着就想笑,这帮人,变脸比翻书还快。
“不去。”她干脆利落地回绝,顺手挂断电话。
研讨会?
呵,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她拨通另一个号码,语气带着几分挑衅:“陈工是吧?想聊‘城市感知’?明早七点,丙三路井盖见。不见不散。”
第二天清晨,丙三路段,寒风呼啸。
于佳佳裹紧大衣,站在那锈迹斑斑的井盖旁,像一棵倔强的白杨。
没过多久,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陈砚田推门而出。
他依旧是那副一丝不苟的模样,金丝边眼镜在晨光下闪着冷光。
两人并肩而立,一辆老式电车“哐当哐当”地驶过,脚下的井盖传来一阵轻微的震动。
“陈工,”于佳佳打破沉默,声音清冷,“您觉得,这算事故预警,还是城市呼吸?”
陈砚田沉默了。
他摘下眼镜,用丝帕仔细擦拭着,仿佛在思考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半晌,他重新戴上眼镜,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支钢笔,打开那份所谓的“城市感知标准草案”。
只见他龙飞凤舞地在页写下一行字:“允许部分基础设施保留可感知振动。”然后,毫不犹豫地撕掉了另一页,那上面赫然写着:“全面静音化改造”。
纸张撕裂的声音在寒风中格外清晰,像是一声叹息,又像是一声解脱。
临走前,陈砚田低声说道:“我父亲是铁路养路工,他教我听铁轨唱歌。”
于佳佳望着他略显佝偻的背影,若有所思。
她伸出脚,用鞋跟轻轻点了三下井盖。
这次,不是什么劳什子的仪式,而是确认,确认这水泥之下的脉搏,还在跳动。
她拿出手机,飞快地编辑了一条短信出去:“鱼已入网,收!”
鼓声事件后,城市中无形的暗流涌动,于佳佳如同一个精密的操盘手,掌控着棋局的走向。
林小满也没闲着,她张罗着把“城市感知工作坊”搬到了城郊一座废弃的泵站里。
说是泵站,其实就是个破旧的砖头房子,四面漏风,墙上还爬满了瘆人的爬山虎,白天都阴森森的。
“这地儿…能行吗?”姚小波挠着头,一脸嫌弃地看着斑驳的墙壁,差点没忍住个朋友圈吐槽。
林小满却像现了宝藏,撸起袖子,眼神里闪着光:“这才叫原生态!懂不懂?真正的城市感知,就要从这种被遗忘的角落开始!”
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期招募通知一出,报名人数直接爆炸,四十二个名额瞬间被抢空。
要知道,这可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培训班,来的都是些“边缘人物”——环卫工、快递员、盲人按摩师……
开班第一天,学员们挤在狭小的泵站里,面面相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微妙的尴尬。
“我说…咱们又不是专家,能听出个啥?”一个穿着泛黄工服的环卫大叔忍不住嘟囔。
林小满微微一笑,打开一台老旧的录音机。
一段单调的声音传了出来——那是赵工在不同天气、不同时间敲击同一根水管的声音,沉闷、清脆、嘶哑,细微的差别,却蕴含着丰富的信息。
“专家写报告,坐在办公室里,对着冰冷的数据指手画脚,”林小满的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而你们,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亲身感受着城市的脉搏,记得城市的冷暖。”
“你们才是真正的城市聆听者。”
这话说到了大伙儿的心坎里,一下子拉近了距离。
接下来的课程,与其说是培训,不如说是一场集体会议。
大家七嘴八舌地分享着自己独特的“听觉经验”——下水道井盖的“咕噜”声、电车轨道摩擦的“吱呀”声、老槐树在风中摇曳的“沙沙”声……
这些声音,在城市喧嚣中常常被忽略,却承载着无数人的记忆和情感。
课程结束时,每人领到了一只简易的振感贴片,巴掌大小,其貌不扬。
“把它贴在你们家门口,或者常经之路,”林小满嘱咐道,“七日后,数据会自动上传到一个匿名共享平台,就叫‘地耳’。”
“地耳?啥意思?”有人好奇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