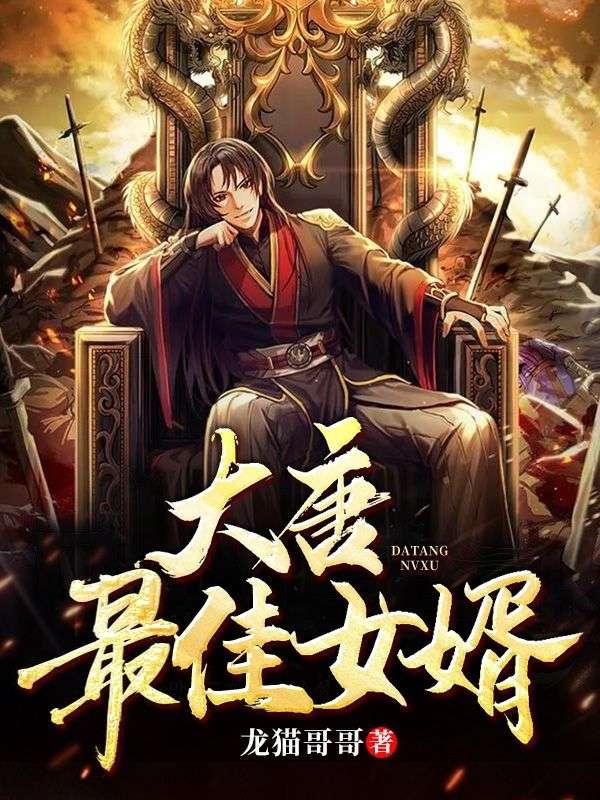富士小说>制霸的意思是什么 > 第544章 老地方速来(第2页)
第544章 老地方速来(第2页)
“白老师,我想请您写一篇文章。”于佳佳说道,“一篇关于城市‘痛觉神经’的文章。”
白烨是位着名的文学评论家,曾经是传统文化的扞卫者。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反思,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时代。
“城市…痛觉神经?”白烨皱了皱眉,“这个概念很有意思。”
几天后,《读书》杂志的头条,刊登了一篇名为《城市的皮肤》的文章。
文章中,白烨用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阐述了“城市应该拥有痛觉神经”的观点。
他认为,城市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更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
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与此同时,于佳佳还组织了十场社区夜谈,主题只有一个:“你听过城市生病吗?”
一位患有哮喘的老人讲述道:“每次附近有施工,我的呼吸机警报总会提前两个小时响起。”
一位住在老城区的居民抱怨道:“自从地铁开通后,我家墙上的裂缝越来越大了。”
这些看似零散的抱怨,被于佳佳整理成一份详细的报告,直接送到了市长的信箱。
两周后,市政府宣布,将“动态感知设计”纳入到市政标准的修订草案中。
在新闻布会上,一位记者追问道:“这是否意味着,以后修路要问工人的意见?”
陈砚田接过话筒,语气平静:“不是问,是听。我们过去只听冰冷的仪器,现在,我们要学会听人的声音。”
镜头扫过台下,赵工坐在角落里,他手里拄着拐杖,轻轻地敲击地面三次。
如同某种确认。
当晚,吴小雨的“痛觉地图”更新上线。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地图上,新增了十五条红色的脉动线。
那是全市十五个“正在自我修复的地基节点”。
这些节点,就像是城市身上的伤口,正在慢慢愈合。
深夜,于佳佳盯着电脑屏幕,那份匿名文件包就像潘多拉的魔盒,缓缓开启。
年的市政会议纪要,纸张泛黄,字迹有些模糊,却散着一股尘封的历史气息。
《关于保留部分老旧管网作为应力释放通道的建议》——标题赫然在目。
于佳佳的心跳都漏了一拍。
应力释放?
感知缓冲带?
冥冥之中,似乎有一根线将它们连接了起来。
提案人签名模糊不清,像被岁月磨损的记忆。
她手指在屏幕上滑动,放大图像,试图从残缺的笔画中找到答案。
赵…?
难道是……?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她立刻拨通赵工的电话,嘟嘟的忙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无人接听。
清晨,她调取了档案馆的监控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