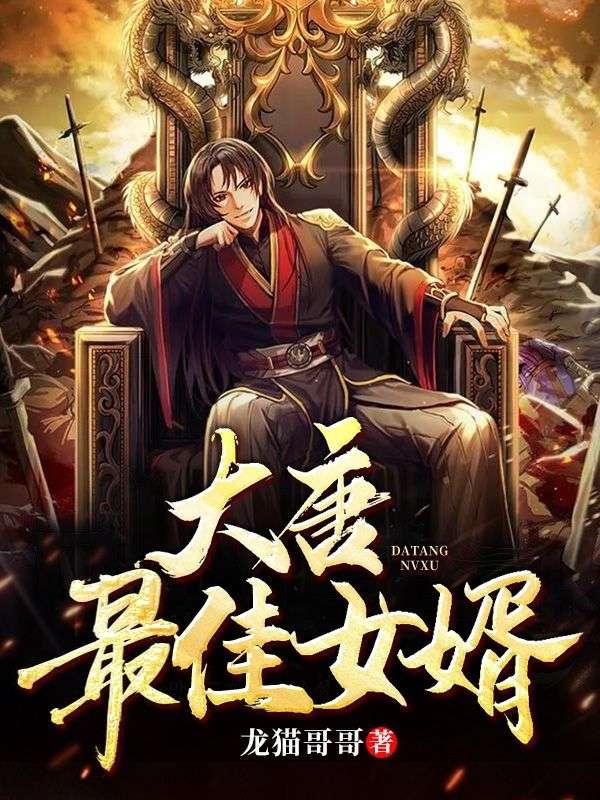富士小说>寻影是什么意思 > 第98章(第1页)
第98章(第1页)
李承志端坐在那张熟悉的檀木诊桌后,头发灰白,神情平和。桌上摊开一叠素白的宣纸,压着老花镜。淡淡的艾草香气,执着地从他手边袅袅升起,混着晨雾的清冷,在小小的院落里弥漫开来,像一道无形的、安宁的界碑,隔开了门外的喧嚣。
“怪病”的阴云已然散去,官方通报早已贴满了镇口的告示栏。可院门口,依旧早早排起了队。男女老少,多是熟面孔。他们脸上带着大病初愈后的些许虚浮,或是被长久焦虑折磨留下的疲惫痕迹,眼神里却有了光,一种劫后余生的踏实和信赖。
“李老大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在儿媳搀扶下坐下,声音带着感激的微颤,“您开的那个安神茶,管用!夜里能睡个囫囵觉了,心口也不那么慌了。”
李承志微微颔首,手指沉稳地搭上她枯瘦的腕脉。指尖微凉,力道却透过皮肤,精准地捕捉着那细微的搏动。他的目光沉静,落在老人松弛的手腕上,仿佛能看见那曾经被恐惧和病痛搅乱的脉络,正一点点归于平顺。
“脉象平和多了,”他收回手,提笔在宣纸上落下几行刚劲有力的字迹,“方子略调两味,再吃三剂。夜里用热水泡泡脚,按按脚心的涌泉穴。”声音不高,却带着磐石般的安稳。
诊桌旁,李氏医馆的几位年轻中医和师承班的学员正忙碌着。他们熟练地分拣着晾晒好的药材,将李承志开出的方子迅速配好,用油纸包得方正严实,再细细叮嘱煎煮的方法。药香混着艾草的气息,在晨光里氤氲升腾。
日头渐渐升高,雾气彻底消散。院门口的人流稀疏了些,但仍有人执着地等着,仿佛这最后一次义诊,是某种重要的告别仪式。
一阵沉稳的脚步声在院门口响起,
带着泥点。王前进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那里,肩上竟扛着半扇沉甸甸、油光锃亮的腊肉,暗红色的瘦肉间镶嵌着晶莹的肥膘,散发出浓郁的烟熏香气。
这分量不轻,王前进走得有些喘,额角挂着汗珠,身上那件畜牧站的旧制服沾着新鲜的泥土痕迹。
“李老!”王前进放下腊肉,那厚实的肉块落在青石板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他抹了把汗,脸上带着略显笨拙的诚恳笑容,“自家灶头熏的!好猪肉!您和医馆的先生们带回去尝尝!五彩镇的水土养出来的!”他声音洪亮,仿佛要用这分量和声音,把心里沉甸甸的感激都倾泻出来。
李承志站起身,绕过诊桌。他走到王前进面前,目光扫过他布满老茧、指缝里还嵌着泥灰的手,又落在那半扇诚意十足的腊肉上,最后定格在他那双依旧布满血丝、却少了沉重阴霾的眼睛上。
“王站长,”李承志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太破费了。救死扶伤,医者本分。这肉……”
“您必须收下!”王前进打断他,语气斩钉截铁,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不光是我的意思!高家村、李家村好些人家都念着您的好!要不是您带着徒弟们义诊送药,好些人那病根儿,哪能去得这么快?”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了些,带着劫后余生的喟叹,“这‘怪病’过去不容易,您就当是咱五彩镇一点土气的心意!”
李承志看着他眼中那份固执的真挚,沉默了片刻。他伸出手,并非去接那腊肉,而是轻轻拍了拍王前进肌肉结实的、沾着泥灰的胳膊。那动作很轻,却带着一种无言的理解和接纳。
“好,”他点点头,“这份心意,我们医馆收下了。替我们谢谢乡亲们。”他转头对旁边一个年轻的中医示意,“小陈,把王站长的腊肉拿到后厨去,晚上正好添个菜。”
王前进脸上的笑容瞬间舒展,像是完成了一件顶重要的大事,长长舒了一口气。
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将葡萄架的影子拉得长长的。院门口的队伍终于散去,最后一位咨询高血压日常调理的大爷也千恩万谢地拿着方子走了。
李承志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眉心,脸上透出长途跋涉后的深深疲惫,但眉宇间却是一片松快。
医馆的弟子们开始安静地收拾药箱、整理剩余的药材,动作间带着一种仪式般的郑重。
“师父,”一个弟子轻声问,“剩下的这些艾条和安神香包……”
“都留下,”李承志没有犹豫,“交给楚楚姑娘。镇上还有些老人家用得着。”
——
暮色四合,五彩民宿的院子里却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几张八仙桌拼在一起,上面铺着洁净的白布。碗碟碰撞,笑语喧哗,混合着菜肴浓郁的香气,驱散了最后一丝疫情的阴霾。
张建树系着那条歪歪扭扭的草莓围裙,穿梭于厨房和院子之间,额头上全是亮晶晶的汗珠,嘴角却咧到了耳根。
他指挥着汤阳、李炎和几个帮厨的邻居,将一道道热气腾腾的菜肴端上桌:红亮的油焖大虾、碧绿的清炒时蔬、金黄酥脆的炸河鱼、浓香四溢的山笋炖走地鸡……最显眼的位置,赫然摆着王前进送来的那半扇腊肉,已被切成厚薄均匀、晶莹剔透的薄片,配着碧绿的蒜苗炒得油亮诱人。
“来来来!都尝尝!自家养的猪,自家熏的肉!香着呢!”张建树声音洪亮,带着当家主人的豪气与感激,“今天这桌,谢天谢地谢大家!没你们,我们五彩镇这道坎儿,真不知道咋过!”
李承志、李荣耀、张静和、南之乔、叶蓁蓁、尹力,张亮、几个博士生、朱晓路、林薇、王前进,还有李乔和舍友们围坐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