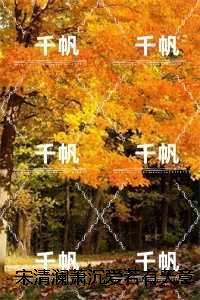富士小说>大明黑莲花原著 > 第29章 家丑外扬(第1页)
第29章 家丑外扬(第1页)
裴老夫人一言不发地沉着脸,激烈的情绪在胸膛翻涌。
要不是裴家做主收养了裴叔夜,他现在不知是在哪个地头劳作的野小子,哪来的这般风光?要他办点事,为家人谋点前程,这是天经地义!
——阿嚏!
正在官署里的裴叔夜猛地打了个喷嚏。
奇怪,这天儿也热了,怎么还能着凉?
正这时,琴山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六爷,属下不是照您吩咐去跟妙雪姑娘的行踪么……”
裴叔夜见琴山支支吾吾,心生狐疑:“有事便说。”
“刚才发现她昨晚压根没回家……而是,被老夫人关到了思过堂里。”
裴叔夜猛地抬起头。
——思过堂那个鬼地方。
他远离后宅太久了,都忘了那个地方会有什么手段。他哪想到她这么狡猾一个人,也会吃这种闷亏。
“蠢女人,我半天不在都不行。”
“诶六爷!”
裴叔夜已经大步往外走去,不过须臾,便见一个身影策马远去。
轰隆,几声闷雷滚滚,却不见雨点,天边翻滚的乌云似在酝酿着一场暴雨。沿海的四月天就是这样,十天里头有七天在下雨,剩下两天阴沉沉,勉强有一天能见着零星的太阳,烈日却将湿气蒸腾起来,活像把人闷在蒸笼里烤。
这天气从里到外都叫人不太舒服。
裴叔夜刚踏入院门,却见母亲一脸怒容地坐在明堂上,裴二奶奶一脸谨小慎微,徐妙雪也跟鹌鹑似的,垂头丧气站在后头。
此刻他还天真地以为母亲这怒气是针对徐妙雪的,正想开口调解,却听得裴老夫人一声怒斥:“跪下。”
裴叔夜愣了愣,还是顺从地跪下了。
他不解地望向徐妙雪。
不对——他分明在她眼里看到了转瞬即逝的幸灾乐祸。
“承炬,我问你,可还记得自已在宗祠里立下过什么誓言吗?”
“儿不敢忘。”
雨点砸在屋瓦上发出万箭齐发般的脆响。
不知为何,徐妙雪心里突然没那么得意了。
她以为他是百毒不侵的六爷,这点小把戏对他来说如同挠痒痒。
可他跪在那儿,好像真的就只是一个无措的儿子。
裴老夫人看向裴叔夜的眼神,那是真的怨恨。
“当年的话,你再说一遍。”
裴叔夜喉头滚动,漫长的停顿后,才沉声道:“天地为鉴,宗亲共证。今承嗣继祧,当以裴门骨血自持。晨昏定省,侍奉椿萱;光耀门楣,不辱宗庙。族中老幼视若血亲,家业兴衰系于已身。若有违逆,天地共谴;若存异心,神鬼同诛。”
声音像是涩滞的河流,被泥堰堵住了去处,茫然地打着旋,徘徊着。
裴老夫人就怕养出了一只白眼狼,她得确认裴叔夜对裴家的态度。
这是他欠裴家的,她要反复提醒他。
“你可知自已做错了什么?”
……
“请母亲明示。”
“你错在自私!”
好大一口锅,连徐妙雪都吓了一跳。她从没见过裴叔夜这么乖巧,受气包似的样子。
她有些傻眼,真后悔自已多此一举,半夜醒来都得扇自已两耳光。
裴叔夜逆来顺受道:“母亲息怒,儿子定改过。”
“那你五哥的事,你是管还是不管?”
徐妙雪万万没想到,裴老夫人能偏心成这样。
这几日就光裴老夫人让裴叔夜办的事,徐妙雪都听说了好几件,不是让裴叔夜去衙门里打点关系,给裴家那几位爷擦屁股,就是叫他去给裴家挣脸面。每回开口必先提这些年裴家的艰难,话里话外都在埋怨——若不是他当年招惹四明公,裴家何至于此?
她以为老夫人发这么大火要训斥的,仍是裴叔夜不肯对四明公低头这事。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 宋清澜萧沉爱若有天意,兜转终可回:结局+番外宋清澜萧沉
- 原来当年出卖父亲的人竟然不是陆风,而是为父亲讨回公道的萧沉。那具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