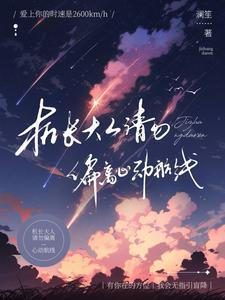富士小说>易卦识凶探案TXT百度 > 第91章 有风经过2 赵京蓉(第2页)
第91章 有风经过2 赵京蓉(第2页)
也是这个时候,荀舒突然意识到,她并不了解李玄鹤。
她曾经以为与他朝夕相处大半年,已足够了解他这个人,可如今才惊觉,她所知道的全部,也不过是一小部分的他,甚至还是他想让她知道的那部分。
她曾问他究竟在忙什麽,他只含糊道,是岐山封禅的事。她也不知道这事儿和大理寺能有什麽关系,难道是预料到会有凶案发生,提前布局预防?但见他不愿意说,也不再多问。
七月底的时候,天气逐渐转凉。
在潮州的时候,荀舒最喜欢在棺材铺里窝着,可如今竟连个能安心窝着的地方都没有。她强迫自己忙碌起来,不仅要查姜拯的事,还要查长生殿的事。偶尔得空,她也不会闲在宅子里等某人,而是抱着竹竿和破布条去集市上摆摊算卦。
总的来说,荀舒很忙,但所有的忙碌都像那镜中月水中花,瞧着好看,但轻轻一碰,方能发现,尽是虚幻。
长生殿和姜拯的事没查出多少有用的,摆摊连一个铜板都没赚到。
她仿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逃避,用忙碌来掩饰不安。
她越来越想念姜拯和棺材铺了。
八月初一,秋高气爽,晴空万里。荀舒一大早便出门,带着阿水和鱼肠,打算去城郊长生殿的神宫看看。
那神宫坐落在城郊的半山腰,前後三进大院子,东西各有跨院,比宁远村的神宫气派得多。前些日子荀舒曾来过一次,知道了不少关于长生殿的事。
比如,与司天阁存在千年不同,长生殿建立不过百年。神宫里的小道士说,司天阁与长生殿本就是同宗,百年前一名司天阁的弟子下山後建立长生殿,自此後一步一步发展壮大。
又比如,十几年前当今陛下寻长生之道,偶然结识了长生殿殿主赤阳子,一见如故,成为道友。等到几年前陛下登基,陛下将赤阳子奉为国师。这之後,长生殿在大梁的各个州县迅速发展壮大,声望渐渐超过了司天阁。大梁大半臣民,都成了长生殿的信徒。大一些的城池,亦争先恐後建立长生殿的神宫。
那一次来时,荀舒没能将整个神宫里里外外转遍,回去後,後悔不已,总担心姜拯被关押在她没去过的角落,是以今日她决定再去一次。
京城的神宫无论何时来都不缺香火,百姓虔诚跪拜,口中念念有词,神宫中烟火缭绕,远远看着像是走水了似的。
院中无树木,少了几分生机,亦少了几分清气。上次来荀舒变察觉到此处气场不对,她劝了几个体弱的百姓不要在此处上供,怕会引来灾祸,得重病,但那几人看她像看个疯子,骂了几句远远离开,仿佛她是瘟疫,生怕沾上一星半点。
也正因为这事,上次荀舒才没能逛完整座神宫。
荀舒看着眼前的人群,莫名想起司天阁山脚下的那个小道观。
司天阁不需要百姓的香火,所以从未建过道观神宫。百年前司天阁的位置意外被世人知晓,这之後有人在山脚下寻了块大石头,当成司天阁的神像,时不时带些瓜果搁到那石头上,之後又将线香插在石头前的泥土里,以天地为炉,燃香求神明庇佑。
再之後,当时的司天阁阁主在祖师爷神像前跪了几日,决定在山脚下建第一座司天阁的观。
那道观不大,只有一间屋子,将那块大石头包入其中。石头前摆了桌案,桌案上只放着一个香炉,供百姓上香。前来拜神的百姓将贡品留在屋子里,司天阁会定期来清理。若是还能食用,便留在这小道观里,等着需要它们的有缘人出现;若是腐败,便拿到山林间埋起来,还给天地。
可惜司天阁早已式微,自她记事起,那位于深山里的小道馆便没什麽人来。即使如此,每隔几年,师父还是会带着她和师兄去修补小道观的屋顶。她曾问师父,既然已没人来了,为何不任他落败。师父却说,即使没人来,若遇到阴雨天,能为山中生灵遮挡些风雨,也是好的。
师父走後,司天阁也散了。上次回山中时也忘了去那小道观瞧瞧,也不知那屋顶如今可有疏漏?是否还有生灵会在其中躲雨。
见荀舒盯着屋檐久久没有动作,一旁的阿水担忧地问:“姑娘可是遇到什麽难处?”
荀舒如从梦中惊醒,笑道:“看那瓦片甚是漂亮,瞧着很贵的模样。”
阿水顺着她的目光看了几眼,点点头:“确实是,瞧着比公主府的瓦片还要漂亮。”
荀舒收回目光,轻声道:“走吧。”
她带着阿水,将神宫里里外外都走了一遍,没有任何发现,正准备离开,到门口时却遇到了方晏。
他今日是一个人来的,双手空空,没带任何贡品,像是打算凭着“之乎者也”,劝说神明降福。
荀舒没想到会在此处碰到他,冲他挥挥手,靠近後俩人寒暄几句,荀舒压低声音,好心叮嘱道:“这地方气场不对,恐怕有邪神。方兄若想找地方求神明保佑赵二姑娘,还是换个道观,或者去找个寺庙也行。总归都是天上的人,都能帮百姓实现心愿,佛祖和神明也没什麽不同。”
方晏面容肃穆,没有丝毫笑意:“阿舒,此处人多眼杂,我们换个地方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