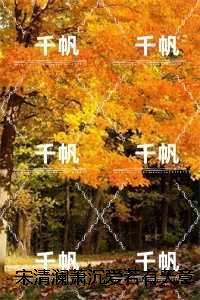富士小说>塔吊五证一书是包括哪些 > 康巴家族(第2页)
康巴家族(第2页)
“诅咒?”
族长沉重地点点头:“我们康巴家族,世代受一种怪病的折磨。男子活不过四十岁,都会像我一样,在壮年时突然衰弱而死。我的祖父丶父亲,还有我的两个兄弟,都是这样死去的。如今,轮到我了。”
漆雕烟霏这才注意到,多吉坚赞虽然头发全白,面容憔悴,但仔细看去,他实际年龄可能不超过四十岁。
“那个年轻人说,这种病并非诅咒,而是一种遗传的血液病。他说,也许有一天,会有一个懂得生死奥秘的报丧者前来,能够帮助我们。”多吉坚赞的眼神中带着最後的希望,“现在,你来了。”
漆雕烟霏沉默不语。她确实懂得一些医术,这是作为天葬师的附加技能。在长期处理尸体的过程中,她学会了辨认各种疾病的特征。但治愈活人?她从未尝试过。
帐篷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帘幕被猛地掀开,一个年轻男子闯了进来。他约莫二十多岁,身材高大,眉眼间与多吉坚赞有几分相似,但更加锐利张扬。
“父亲!您怎麽能让这个报丧者单独与您相处?”年轻人语气激动,“她会带来厄运!”
“嘉措,不得无礼!”多吉坚赞厉声喝道,随即又剧烈咳嗽起来。
漆雕烟霏认出这就是刚才在营地入口用警惕眼神盯着她的年轻人之一。他是多吉坚赞的独子,康巴家族的继承人——嘉措。
嘉措大步走到榻前,挡在父亲和漆雕烟霏之间,目光如刀:“报丧者,我不管你是谁派来的,立刻离开我们的营地!”
“嘉措!”多吉坚赞试图起身,却无力地跌回榻上,“她是我们的客人。。。”
“客人?”嘉措冷笑一声,“她是死亡的使者!自从她踏入我们的领地,族人们就惶惶不安。您已经病重,我不能让她靠近您!”
漆雕烟霏平静地注视着这一幕,缓缓将念珠戴在自己的手腕上,然後把画像小心地收进怀中。
“族长,”她无视嘉措充满敌意的目光,直接对多吉坚赞说道,“我需要查看您的病情。”
嘉措怒不可遏,猛地抽出腰间的藏刀:“你敢!”
就在这一瞬间,漆雕烟霏动了。她的动作快如闪电,衆人还没看清发生了什麽,嘉措手中的刀已经落地,而他本人则被反剪双手,制伏在地。
“我若想害人,你早已没命。”漆雕烟霏的声音冷如寒冰,放开了一脸震惊的嘉措。
帐篷外的守卫闻声冲了进来,见状立刻拔出武器对准漆雕烟霏。但她只是静静地站着,面纱下的表情无人能见。
“都退下!”多吉坚赞用尽全身力气喊道,“她是我的客人!谁敢对她无礼,就是与我为敌!”
守卫们面面相觑,犹豫不决。
嘉措从地上爬起来,揉着发痛的手腕,眼神复杂地看着漆雕烟霏。震惊之馀,他似乎明白了父亲为何执意要请这个神秘的报丧者前来。
“出去,嘉措。”多吉坚赞语气疲惫却坚定,“让我和报丧者单独谈谈。”
嘉措咬了咬牙,最终还是一言不发地带着守卫退出了帐篷。
帐篷内重新恢复了安静。多吉坚赞苦笑道:“请原谅我儿子的无礼,他只是太过担心我。”
漆雕烟霏轻轻摇头,表示不在意。她走近卧榻,仔细观察族长的面色,然後轻轻翻开他的眼皮查看。
“这种病。。。是从什麽时候开始的?”她问道。
“据家族记载,已经延续了五代。每一代的男子都会在三十五岁左右开始出现症状:乏力丶气短丶面色苍白,然後日渐衰弱,通常在四十岁前就会。。。”多吉坚赞没有说下去,但意思不言而喻。
漆雕烟霏若有所思。她确实在多年的天葬师生涯中见过类似的病例,大多发生在一些封闭的家族中。草原上的人们称之为“血咒”,但她知道这是一种遗传疾病。
“我无法保证能治好你,”她坦诚道,“但我可以试试。”
多吉坚赞微微一笑:“无论如何,感谢你愿意尝试。那个年轻人说得对,你果然来了。”
提到那个神秘的年轻人,漆雕烟霏的心再次揪紧。她摸了摸怀中的画像,感受到纸张的质感,仿佛能透过它触摸到那个人的温度。
当晚,漆雕烟霏被安排住在一顶独立的帐篷里。尽管康巴家族的人们仍然对她敬而远之,但至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所需。
她坐在帐篷中,就着油灯的微光,再次展开那幅画像。画中的她比现在年轻些许,眼神还不像如今这般死寂。那是扎西平措记忆中的她,是他离开前的她。
“你到底在哪里?”她轻声自语,指尖轻轻描绘画中人的轮廓。
如果扎西平措还活着,为什麽不去找她?如果他已经死了,又是谁留下了这些线索?
无数疑问在她心中盘旋,让她多年来第一次感受到了除麻木以外的情绪——希望。
帐篷外传来轻微的响动。漆雕烟霏立刻警觉地收起画像,熄灭油灯,悄无声息地移动到帐篷入口处。
帘幕被轻轻掀开,一个身影闪了进来。漆雕烟霏立即出手,将来人制住,一把冰冷的匕首抵在对方喉间。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 宋清澜萧沉爱若有天意,兜转终可回:结局+番外宋清澜萧沉
- 原来当年出卖父亲的人竟然不是陆风,而是为父亲讨回公道的萧沉。那具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