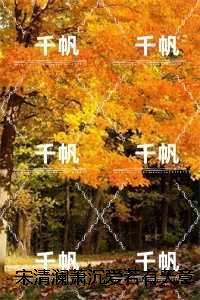富士小说>男朋友送礼物都是几十块钱的 > 第100章 华丽囚笼 我和她真的再也回不去了(第2页)
第100章 华丽囚笼 我和她真的再也回不去了(第2页)
阿姨也意识到情况的不对劲急忙奔下楼。
方轻茁附耳贴在木格玻璃门细细聆听,没有任何响声,只有他擂鼓的心跳,但听久了似乎有流水的哗啦声,随手抄起把椅子,对准油砂玻璃用力连砸三下,门板砸出个口子,他伸手进去将门锁从里面打开。
浴室没开灯,敞着半扇窗,灰扑扑的阴天没有什麽好的光线,骆姝以背对他的姿势半跪半趴在浴缸壁缘,昨夜还生动的小脸如今惨白,没有意识地枕在半条胳膊上,肘部往下的部分埋进水龙头还在出水的浴池里不明状况,而另一只手无力地垂落身侧,最冲击视线的是一旁摔在地砖的玻璃杯碎片。
方轻茁悚然,喉咙不觉间有些干,顿时连呼吸都缓慢起来,一个可怕的可能充斥脑海,他动了动腿想要靠近,却发现双脚根本不受他控制,全身的血液更是从这一刻起倒流。
意识到这样不行,他尝试着迈腿,迈出的每一步都需要组织莫大的勇气。
仅差最後半步就能看到缸内,方轻茁依旧紧张地负重挪动,後背和手心不知不觉冒出冷汗,好在,映入眼帘的缸内洁白无瑕,好在,水还是水的颜色。
似得到点慰籍,他冲过去一把从水里捞出那条手臂认真检查,浸湿的衬衣袖口笔直地往地毯上滴水,庆幸的是,皮肤,指头乃至血管哪里都是完好无损。
理智好像恢复了些。
方轻茁赶紧扶起骆姝没有什麽支撑力的脖子,颈动脉的搏动震得他掌心发麻,是虚惊一场。
吊在嗓子眼的那份担心总算散开,他将人小心翼翼地揽入怀,後怕般牢牢抱紧,如同在拥抱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宝,压抑到极限的情绪化作泪腺的一颗眼泪,紧接是第二颗第三颗,他感觉不到自己抱着骆姝的力度到底有多大,只觉得从这个瞬间开始又活了过来。
晕倒的是骆姝,可感到劫後馀生的是他。
骆姝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仍在那间华丽囚笼,她艰难地爬坐起来,四肢软绵完全使不上力,刚准备下床就被手背传来的拉扯疼感截停,吃痛地倒吸凉口气後举目望去,手背血管插着针,原来是输着液。
她的细微动静很快把屋内的另外一个人吸引过来。
“孩子,你醒了。”
骆姝循着声音源头察看,一位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老太太,见又是张生面孔,索性缩回被窝耷拉着脑袋不搭腔。
老太太也没有要责怪的意思,端着笑把她的冰凉小手兜在手里取暖:“你是低血糖犯了,我叫人给你送些吃的。”
骆姝还是不肯说话,一整天没进食又被困在房间闷出一身汗,想着先清理下,没走两步就两眼发黑直接栽倒在浴缸旁。
半醒半昏间,她感觉有人不停地贴着自己悔过道歉,浅意识告诉她那人是方轻茁,因为她迷迷糊糊喊了声“方轻茁”,那人应得又急又快。
于是趁着那股恍惚劲她又提出要回去的要求,几乎是下一秒,在她彻底昏睡之前,她听见:“好,我答应你。”
骆姝本想问方轻茁在哪儿,可擡眼的刹那瞥到窗外的浓稠夜色,虚弱身体脱口而出的却是坚定的四个字:“我要回去。”
在老太太安排下,骆姝如愿出了房门还坐上了老太太的专车。
临走前,仿佛是对视线比较敏感又或许感知到什麽,她透过车窗去望头顶的二楼阳台,不知是不是错觉,依稀有抹人影晃过。
眨眼的工夫,车子如离弦之箭啓动,视野里的不确定画面一划而过只剩下虚影。
入了夜的别墅万籁俱寂,相较白日的小打小闹和风,夜晚的山风势头更猛,方轻茁独自躲在房间里,放任尘世的喧嚣将他淹没。
黑暗环境下,人的听觉总要比以往灵敏。
房内没开灯,老太太一进去,缩在床脚的方轻茁立马别开脸。
老太太没揭穿他的拙劣演技,而是走到床边坐下柔声劝慰:“人,奶奶已经帮你安全送回去了。”
方轻茁周身的低气压早已敛去,吸了吸鼻子:“谢谢奶奶。”
身为奶奶哪见得了孙子难过:“有什麽别憋在心里,和奶奶说。”
“那,她有说什麽吗?”方轻茁半犹豫半含期待地问。
老太太心里直叹气,但也不想骗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回去。”
“她,她没事就好,就是,她应该,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方轻茁嗓音里慢慢透出一丝将近崩溃的颤抖,随着话音的断断续续哭腔尽显。
风将窗帘吹扬起来,捎上他的额发,露出眼里的破碎。
那抹後怕直到现在仍缠着他,困住他,从心脏慢慢绽放开,然後顺着每一根血管蔓延。他不敢面对骆姝,连目送也是躲在角落偷偷目送,说不定这一面将会是最後一面,他发誓,他真没想过要把她逼到那步,就像祝婕那样,每每回想起来都忍不住的战栗。
“我也是没办法了,她倒在里面的那一幕,我怕得要死,可我怎麽总是在食言,答应她的话答应她的事一件都没实现,我活该,不值得同情,明明她都快松口了,怎麽又被我打回原形,回不去了,我和她真的再也回不去了。”
他支支吾吾说了半天前言不搭後语的话,好比食肉动物露出最致命的弱点,吐露一切不能言的悲伤,“我再也不敢逼她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奶奶我真的错了。”
百毒不侵的方轻茁,只有自己知道是如何一步步沦陷,再如何一步步堕落,然後固执,举步维艰地维持这场美梦,妄图美梦成真,最後差点儿成真的是噩梦,他是那个刽子手,最深的那一刀是他自己捅的。
他甚至不敢闭上眼,一旦闭上眼刻进大脑的真是场景就会冲破重重阻碍扑面袭来,他错的太多了,一败涂地且无力回天,只能嚎啕大哭像个犯了错的小孩一头扎进奶奶怀里不断重复着我真的错了。
这一刻,年过半百的老太太仿佛在孙子身上看到了儿子的影子,历史好像在重新上演,但又没有。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 宋清澜萧沉爱若有天意,兜转终可回:结局+番外宋清澜萧沉
- 原来当年出卖父亲的人竟然不是陆风,而是为父亲讨回公道的萧沉。那具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