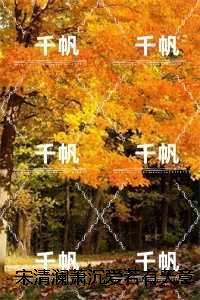富士小说>刚谈恋爱男朋友送了很多礼物怎么办 > 第87章 苏黎世 没有方轻茁的人生不该笑吗(第2页)
第87章 苏黎世 没有方轻茁的人生不该笑吗(第2页)
夏以茉作壁上观结束,慢慢啓口:“反应这麽大,就那麽怕他把花抢来送你?”
骆姝顿觉失言,贴在身侧的手指不自然地动了动:“毕竟他是我带过来的,佳倩结婚,他在这又蹦又跳,不合适。”
“我没意见啊。”谷佳倩不知何时走来,“就当看马戏团表演了,不过,你们什麽进展呐,两个大男人竟当衆扯头发抢捧花。”
夏以茉:“可不关我俩事。”
骆姝快速接茬:“纯属他们脑抽。”
谷佳倩意有所指地笑笑:“我还以为是有人好事将近,花都抢了,下一步是不是打算求婚。”
“本小姐单身。”夏以茉满不在乎地把玩头发,“再说了,谁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是朵交际花,哪哪都瞎嘚瑟?”
此话一出,骆姝和谷佳倩皆付之任重道远的同情目光,可几米开外受到同情的主人公却浑然不觉,全身心扑在赢了方轻茁的炫耀里。
晚上的喜宴搭在露天小院里,欢声笑语觥筹交错充斥在整片黑幕下,方轻茁原本估摸着今晚吃席怎麽也能挨着骆姝入坐,顺便问问她今天喊他是有什麽要说,结果谁知会按照风俗男女分桌,他一边腹诽深城就没那麽多讲究,一边掠过身旁大快朵颐,直打饱嗝的庄赫,还不如上回呢,起码就隔着两个人,真是越活越不如从前。
生无可恋间,换上一袭修身对襟龙凤褂的谷佳倩挽着新郎踱到他们这一桌敬酒。
一番客套寒暄後,谷佳倩突然坏心眼儿地为难起方轻茁:“不好意思啊,事先不知道你要来,没房了。”
新郎官表情有一瞬间的空白,并未发表过多意见,只是牵起嘴角顺着谷佳倩说了声抱歉。
庄赫倒是十分慷慨地接纳他:“大不了和我挤一晚……”
岂料,方轻茁想都没想拒绝:“没事,我睡车里。”
说这话的时候故意扯开嗓子,有意无意地往馀光方向瞟。
夜沉淀了好久,一派红色汪洋里人声依旧鼎沸。骆姝却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前院的鹅卵石小道上徘徊不前,不承想,迎面撞见瞎转悠的庄赫。
庄赫率先热情打招呼:“咦,骆姝学妹,这麽晚了,你去哪儿啊?”
骆姝随口胡诌:“我就出来顺便逛逛。”
庄赫往她臂弯挂着的薄毯撂去一眼,快人快语:“拿着毛毯出来逛逛?”
陡然被拆穿,骆姝“我我我”半天也给不出个合理解释,索性不吭声紧盯面前这位始作俑者。
教人难堪的话已然说出,再改口太显虚僞,庄赫抱歉地堆起笑脸:“要是没事,咱俩聊聊?”
两人登上供游客合影留念的观赏台,庄赫一屁股坐在那老竹椅上,抄起把蒲扇像是热惨了狂给自己扇风:“听夏以茉说,你在苏黎世念完书就世界各地跑?”
骆姝坐在另一头,与他热化了的松弛表现比简直是心如止水:“也没世界各地,就办婚礼比较热门的那几个地方。”
“难怪。”庄赫作若有所思状。
骆姝略皱眉,不解:“难怪什麽?”
铺垫了那麽多,庄赫总算切入正题:“这五年你就不好奇他是怎麽过的?”
晚风轻拂,老榕树簌簌作响,骆姝装聋卖傻:“谁?”
庄赫环胸,往後靠了靠,老竹凳立马发出嘎吱嘎吱响声:“还能谁,我那自作自受的冤种兄弟呗。”
几乎是尾音落下的同一时间,他目光定在对面,神情严肃而认真:“你刚走那会,夏以茉她们守口如瓶,谁都不肯透露关于你行踪的半个字,之後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隔三岔五出国,起初大家都不知道他飞去哪飞去干嘛,权当他出差散心,要不是一次庆功宴上他喝得烂醉说漏嘴,念叨深城直飞苏黎世的航线为什麽停了,然後抱着我哭诉航空公司的不是,还提议要买下一条航线,他第一次哭鼻子我稀罕得不得了,掏出手机就是开录,准备日後笑话他,结果录着录着就发现不对劲,他说……”
庄赫顿了顿,叹出口气,“他根据给你做的app定位找到了你的交换学校,你的家庭地址,还有你常呆的美术馆,常吃的中菜馆,他说他不明白也不理解,你一走了之,狠心抛弃他,理应过得称心开心才是,可你为什麽老偷偷躲起来抹眼泪呢?新的人生,没有方轻茁的人生,不该笑吗?”
自庄赫的第一句话起,骆姝的脑子就不受控制地乱成一锅粥。不为人知的一面被残忍揭露,是两个人的惨痛血泪史。
她还没整理好要以什麽心态应对,又听见庄赫说:“还有个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讲,起因是他有段日子老带伤上班,我就趁着他不清醒问了一嘴,换来他痛骂了一晚上欧洲人,就是当地熟知的那四类,他一个劲说错了,说内疚,说以为依你的性格换了新环境会适应得很快,可他远远低估了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
庄赫适当的停顿给了悲怅有机可乘,骆姝感觉心尖被轻轻刮了一刀,划破皮的那种,不疼,就是呼吸时堵时顺。她不敢动弹,恐牵一发而动全身,殊不知这只是开胃前菜,宰杀仍未结束,犹如通了电的冲击钻来势汹汹,撕心裂肺。
“我们游戏正式公测那天,他就带头响应啓动新项目,一条命分两条活,一天掰成两天用,唯二的吃饭时间还是从时间缝里挤出来的。”庄赫提到这儿就回忆满满,“就是苦了我,没日没夜地陪他爆肝熬夜,有一次我实在熬不动了就问他为什麽这麽拼命,你猜他怎麽回答的,他说他买了套房,得赚钱。”
骆姝耗尽全身力气掐住大腿肉,故作轻松地开玩笑:“哪里的房子还需要他买,除非……”
“对,买了苏黎世的房,因为你爱去的那家中餐馆倒闭了,所以他偷偷买下你隔壁的那套房子,还雇了个华人阿姨以邻居以同乡的名义给你送餐。”
所以她碰上的眷顾和巧合,不是上帝怜悯,都是方轻茁刻意为之。
“就这样持续到第三年,你应该是察觉到什麽把app卸了,离开了苏黎世,他就再也没出过国。”
方轻茁给她设计的两款app,骆姝出国後就留了比较实用那个,她记得是平安夜那晚收到条更新消息,怕开发者感知到什麽才卸载的。
庄赫还在继续,“混沌那款游戏里有隐藏地图,单独的剧情线,具体是什麽内容连我也不知道,我想只有你登录了才能看到。”
“有一句话说得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和夏以茉都能看出你俩分开,过得那叫一个,痛苦,是,我兄弟对不住你,但起码有一点他很磊落,对比一些男人无脑地求原谅发毒誓,耍嘴皮子功夫,行动力这块他是真男人,今晚的这些,我相信,要是你不问,这辈子他都不会主动跟你交底。”
“还有当年的那笔糊涂账,详细的时间线我虽然不是特别清楚,但他和那俩发小之间早就闹崩了,在你们公开恋爱之前,这个你可以亲自去问他。”
“至于那场车祸吧,的确是他太偏激,但他属实没办法了,他就是知道你有多无辜,多委屈,才无奈出此下策,他捅的篓子太大太逆天了,和他接触那麽久,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他绝不是个不理智的人,如果不是没有後路,他不会以死相逼。”
庄赫走後,视野开阔的观景台仿佛陷入了无尽的茫然无措中,就连夜风吹到这儿都像是受到影响一样,断在了榕树茂盛的树叶上,断在了鬓边的一缕头发丝上,断在了那条盖在骆姝腿上要给某个人在车里过夜的薄毯边角上。
那点记忆,说了不要,统统送人的半年记忆无孔不入地困住她,缠着她,侵蚀她。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 宋清澜萧沉爱若有天意,兜转终可回:结局+番外宋清澜萧沉
- 原来当年出卖父亲的人竟然不是陆风,而是为父亲讨回公道的萧沉。那具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