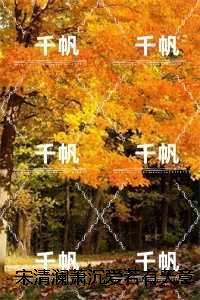富士小说>寡妇门前疯世子百度 > 第77章(第1页)
第77章(第1页)
穆琰瞥了她一眼,神情自若地往榻上一趴,“衣裳脏了,省的污了床榻。”
他说的理直气壮,也的确是事实,容宁无话可反驳,只垂头低声道:“我去唤小厮来替你擦洗上药。”
说着逃也似地往外走去,可还未及走出一步,手腕一紧,已然被他牢牢攥住。
力道不重,却也不肯让她轻易挣脱,他侧首,抬眸望向她,声音暗哑,“我不要他们,粗手笨脚的。”
容宁别过脸避开他眸光,“那那我去唤小月来。”
穆琰蹙眉,“我不用婢女。”
容宁指尖微颤,唇瓣张了张,却再说不出话来。
暖黄光晕拢在她身上,柔美极了,穆琰望着她,手上用力,手臂内收将她拉近自己,低声哄诱似地,“我都为你被打成这样了你合该亲自照顾照顾我吧,嗯?”
声音虽轻,却带着几分若有似无地恳求意味。
容宁心尖儿一颤,抿紧唇瓣儿,手上一挣欲要抽出手离去,穆琰指尖骤然一紧,紧扣在她腕上,微微颤着。
“别走。”他哑声。
容宁垂眸,不由得回首,正撞上他那双漆黑幽暗的眸子。
烛光映照下,他眸色深邃如潭,似蕴着万语千言,翻涌着她读不懂的情绪。
她喉头一哽,良久终是低声道:“我去打水,再取些金疮药来。”
夜风轻拂窗棂,烛光轻晃,映照着容宁进进出出忙碌的身影。
她打来热水,拧了布巾,轻轻替他擦拭。
温热柔软的布巾在肌肤上缓缓拭过,小心避开鲜血淋漓的伤口。
穆琰背上鞭痕狰狞可怖,新伤叠着积年旧疤,层层叠叠,触目惊心。
容宁手中布巾微滞,心口堵的发紧,忍不住开口问他:“王爷他从前也这样打你么?”
穆琰沉默了片刻,只淡淡地,“习惯了。”
短短三个字,落在容宁耳中,却钝刀子割肉似地,沉痛极了。
她都能够想像得到,一个幼年丧母的孩子,在不怀好意的主母和严苛父亲的膝下,能从庶子成为世子,该是怎样艰辛的一条血路。
她轻轻擦拭过那累累伤疤,这条路上的每一步,必定都艰难至极。
清理好血污后,容宁取出金疮药,指腹轻轻蘸了些,细细涂抹在破损的皮肉上。
药膏清凉镇痛,她低着头,神情专注,一点点仔细推开抹匀,没有丝毫马虎。
穆琰伏在枕上,侧过脸来静静凝望着她。
她眉眼沉静,殷红唇瓣儿轻抿着,一副心思全在他身上,温柔得让人心口发痒。
凝望了她良久,他忽然低声开口,“我竟不知,你还会跳南昭鹤舞。”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 宋清澜萧沉爱若有天意,兜转终可回:结局+番外宋清澜萧沉
- 原来当年出卖父亲的人竟然不是陆风,而是为父亲讨回公道的萧沉。那具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