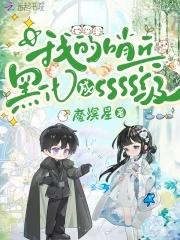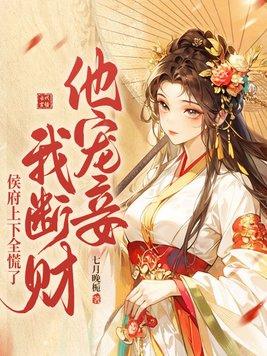富士小说>宋瓷今天也在拯救悲剧吗 > 第13章(第1页)
第13章(第1页)
二流子突然打了个寒颤,像是被什么可怕的东西盯上了,结结巴巴道:"三、三天前有个蒙着脸的人,给了我们粮票说要让这知青在整个大队待不下去"
温之远眉头紧锁:"长什么样?"
"真没看清"二流子的同伴插嘴,"就记得右手腕上有道疤"
雨势渐大,水珠顺着巷子两侧的屋檐滴落。舒月与温之远交换了个眼神,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凝重。
温之远心中泛起一丝疑虑。
他与舒月分明是同一天抵达这个陌生小镇的,自下火车起便形影不离。
在他的印象里,舒月待人谦和有礼,从未与人结怨。
更蹊跷的是,那几个混混口口声声说"三天前"就有人指使他们找麻烦,可三天前他们明明才来到这个地方。
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少年,怎会与人结下这般仇怨?莫非舒月身上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但看他方才应对时的神情,分明也是一头雾水。
事情愈发显得迷雾重重。
"走,把他们送派出所。"舒月轻挑眉头,语气坚定,"单凭我们肯定查不出幕后主使,交给公安同志处理最妥当。"
地上三人闻言顿时哀嚎连连:"大哥饶命啊!该说的我们都说了,您高抬贵手"舒月却充耳不闻,借着箩筐遮掩,在商城上买了根粗麻绳,利落地将三人捆成粽子。
在路人好奇的目光中,两人押着混混往派出所走去。
镇上的派出所门庭冷落,唯有一位白发老者捧着搪瓷缸在门口纳凉。
这支奇特的队伍引得路人纷纷驻足,不时有人打听原委。
舒月也不避讳,边走边将事情经过娓娓道来。
起初还骂骂咧咧的三个混混,眼见围观者越聚越多,顿时面如土色,恨不得把脑袋埋进土里。
那年头百姓最恨这等地痞无赖,若非连烂菜叶都金贵,怕是要用菜帮子砸得他们满头包。
派出所的老门卫见状,惊得差点摔了茶缸,扯着嗓子就往里喊人。
不多时,民警们倾巢而出,待弄清来龙去脉,个个哭笑不得。
做完笔录,负责案件的公安正色道:"情况我们已经记录在案,会进一步调查。若查证属实,我们会派人去青山村通报。"
"辛苦公安同志了。"
"这是我们的职责。"
走出派出所,舒月转向温之远:"我东西都置办齐了,陪你去供销社转转?对了,方才你怎么会"话未说完,就见温之远极其自然地接过他手中的被褥,若不是舒月坚持,怕是连箩筐都要抢过去背着。
"恰巧路过巷口,听见动静就看了一眼。"温之远说着从军绿色挎包里掏出四个油纸包,"来时在国营饭店买的包子,还热着,你垫垫肚子。"
舒月迟疑片刻,腹中适时传来轻响。也罢,既然人家诚心相赠"多谢温知青。"他接过包子,油纸传来的温度恰好暖了微凉的指尖。
雨幕中,舒月嘴角微微扬起。这个人类,倒是出乎意料地可靠。
他紧了紧背上的竹筐,忽然觉得这阴雨天也没那么冷了。
温之远听着舒月客套的称呼,心里莫名有些不是滋味。
"同志""知青"这样的称谓,总像是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
他微微蹙眉,温声道:"往后叫我之远就好,不必这么生分。我们应该算是朋友了?"
舒月正专注地拆着油纸包,热腾腾的麦香混着肉香扑面而来,那香气仿佛能熨平所有皱褶的心事。
他胡乱点着头,腮帮子已经塞得鼓鼓的——吃人嘴短,爱叫什么叫什么吧。
不过转念一想,"之远"是两个字,自己的名字也是两个字,这样称呼似乎有点亏?难不成要让对方叫自己"月月"?这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掐灭了,太像姑娘家的闺名了。
见他出神,温之远误以为包子不合口味:"是不是凉了?"
"唔"舒月慌忙摇头,含糊不清地解释,"好吃得很,大师傅手艺真绝。就是"他咽下嘴里的食物,"我叫你之远,你该叫我什么?舒月听着怪正式的,要不"
话未说完,温之远心头突然一酸。
这孩子竟连包子都觉得稀罕,往日过得是什么日子?他不动声色地接话:"就叫舒月挺好,朗朗上口。,你的名字很好听。"目光扫过少年背上的箩筐,"这些都是新添置的?"
舒月早有准备,语气轻快:"是老家长辈寄来的。我爹娘"他顿了顿,"总之多亏了他们。"
温之远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
昨日初见时就注意到,这孩子的行装单薄得可怜,连过冬的棉被都没有。
如今看来,竟是父母全然不管不顾。幸而有长辈暗中照拂,否则
两人说话间已走到供销社门前。
人潮汹涌,声浪扑面,舒月不自觉地绷紧了脊背。
街道上尘土飞扬,间或夹杂着牲畜的膻味,混着烈日下蒸腾的汗气,让他喉头发紧。
但很快,头顶飞舞的票据、墙上斑驳的标语,还有柜台后此起彼伏的吆喝声,竟奇异地安抚了他——这就是鲜活的人间烟火啊。
既然所需已备齐,舒月便安静地跟在温之远身后。说来也怪,那些对旁人爱搭不理的售货员,见到温之远时总会缓和脸色。青年温润的眉眼像是能化开三尺寒冰,连带着办事效率都高了几分。
70年代小可怜v重度颜控小知青9
舒月直勾勾地盯着温之远的脸,目光灼热得让温之远耳根发烫。
他下意识摸了摸脸颊:"我脸上沾了什么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