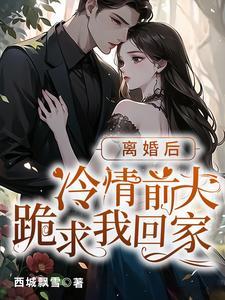富士小说>快穿之女配为王免费 > 第52章 大女主文里的炮灰女配六(第2页)
第52章 大女主文里的炮灰女配六(第2页)
她的风格也愈加分明:偏重写实,讲究光影与质感,绣出来的东西几乎可乱真。
她绣的鹤羽,根根分明,风一动便似要凌空飞起。行家看了也惊叹,这不像画的,不像绣的,像是从眼前实景里,活生生“扣”下来的。
而林青禾却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她所绣之物,并不拘于形色分明,而重在“意”的传达。她常绣山川草木,却不求枝叶分明,而用留白丶断线与巧色点染,营造出烟岚缥缈丶水光浮动之感。
她的绣,不在眼前,而在心里;不是描摹眼见,而是刺绣人心所向。
若说杨知意是“以眼绘物”,林青禾便是“以心写意”。
两人一刚一柔,一实一虚,风格泾渭分明却又互为映照。民间有人言:“杨家绣坊,半为人间真景,半为梦中诗画。”
*
苏州水路纵横,春夏交替之际,天光正好,万物华盛。
知府五十大寿,早已在坊间传得沸沸扬扬。此次寿宴,沿着苏州城南的元河设宴,整条河道皆被封禁,只许寿船往来。大小画舫三十六艘,金灯彩帷,连绵如织,宛如一条流动的锦带。
中央一艘主船名为“长乐”,雕梁画栋,金漆朱柱,乃苏州三年未动的大型官船。主船高挂红灯,顶上系着“寿”字巨幅丝绸,金光灿烂,直可晃眼。
船头设戏台,舞伎穿轻纱如雾丶足蹈莲步,丝竹绕梁。船尾又有舞狮跳鼓,龙舟灯影穿梭不息。
还有水上技艺之人,乘着小舟高杆翻跃,扬水如珠帘,献上“龙腾寿海”丶“鹤舞长空”等吉祥之景。
席宴设于主船与副船之间,三十六席依次铺开,官员商贾丶文人艺士丶绣坊主事皆列席。
知府大人坐于高位,面色红润,左右子嗣陪侧,言笑晏晏。
*
杨家也被邀请在内,她站在副船上,远远望着那艘最大的寿船,心中有一种静到极致的期待。等了整整五年,这一夜终于来了。
杨知意的经历说是天才陨落的悲剧,不若说是民斗不过官的典型案例。在这个重视身份丶强调阶级的古代,弱者从来没有声音。
杨知意上辈子告不了尤宴初,除了她没有证据,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她没有权势。
她奈何不了他。
但是今天,今天,她终于凭借着和林青禾“双姝”的名声,来到了知府大人五十岁的寿宴上。五年来的所有磨炼,都是为了这一刻——为了让她的绣品,光明正大地出现在贺寿礼单之中。
更何况,这场寿宴的主角——苏州府知府,乃是一方父母官,不仅统辖一府之政,更掌着江南贡品的复审之权。
而“杨家绣坊”这几年名声渐盛,尤其“并绣双姝”的传说,在江南早已传开。知府大人素闻其名,他特意吩咐人将杨家绣坊所呈之物取上主船,一观真容。
*
杨知意此刻,正同林青禾静静地站在主船後段的舷窗边,身後锦匣中是她们亲手绣的贺礼。
帘外人声鼎沸丶灯火辉煌丶觥筹交错丶欢声笑语。这一切都不过是戏前的鼓吹,是在酝酿丶在催熟。
“喧哗得好啊,”她低低说了句,“人人都已在席,就等主角上场了。”
林青禾疑问了下,“什麽?”
杨知意淡淡看了她一眼,摇头不语。
尤宴初,你怎麽也想不到吧。你自以为是的体面丶你眼下醉眼朦胧的得意,甚至这河上铺陈的灯火,都会照见你的真面目。
这艘画舫,这高门显赫的宴席,就是你万劫不复的坟。
![[红楼]林家天骄+番外](/img/4593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