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小说>快穿之女配为王免费 > 第66章 大女主文里的炮灰女配二十(第1页)
第66章 大女主文里的炮灰女配二十(第1页)
第66章大女主文里的炮灰女配(二十)
京城繁华,寸土寸金。杨家虽积年经营,颇有些家底。然要为新科进士丶点入翰林院为编修的女婿邵明溪与长女杨知静觅得安居之所,仍费了一番斟酌打算。
最终择得了一处略为偏僻的宅院,地段虽不显赫,却清静雅致,既不张扬,又与邵明溪初入仕途的身份颇为相宜。
与此同时,杨知意和林青禾奉旨入宫,两人皆通过考核後,入尚服居听用。
入宫未久,宫中传旨,召杨知意与林青禾同赴御书房。
彼时正值日午,阳光斜洒金砖御地,御书房内香烟袅袅,帘影摇曳。皇帝着常服,倚坐明黄九龙椅上,面容沉静,眼神却锋利如刃,似能看透人心。
林青禾尚年幼,从未曾亲睹圣颜,一路随行已觉脚下虚浮,入殿之前更是瑟缩不语。见皇帝坐于九龙椅上,眉目不怒自威,竟忍不住轻轻颤抖,额际沁出细汗。
*
皇帝目光扫来,声音低沉而不容置疑,“听闻尔等将染艺传授于织女工匠,其中尤有出身寒微者。此举,出自谁意?为何如此?”
林青禾低着头,连话都不敢答一句,手指紧紧绞着衣角。
杨知意见状,便上前一步,俯首叩地,稳声应道,“啓禀陛下,此事出于臣女之意。臣女以为,技艺藏于一家,不过小富小贵。若能将此技传与出身微寒者,则能使他们有所凭依,既可脱离困厄,亦能自立于世。此其一也。”
她顿了顿,见皇帝面色平静,继续道,“其二,新布料丶新染法之出现,必将带动织造丶刺绣乃至成衣各行各业。譬如苏绣丶湘绣丶粤绣丶蜀绣,虽各有千秋,然皆需上好布料为基。若布料颜色更为丰富丶质地更为优良,则绣娘们巧思得以尽展,绣品亦能更上层。如此,不仅苏绣一地,整个天朝的绣业都讲因此受益。”
“万千绣娘生计有了着落,亦能促进市面繁荣,于国于民,皆有裨益。”
皇帝微微颔首,却又道,“话虽如此,然好物当先供于宫廷,彰显天家威仪。若寻常百姓皆能轻易用之,宫中威仪将安所寄?”
此言一出,林青禾几乎站立不稳,低着头,一言不发,连气息都屏得极轻。杨知意却微垂眼帘,心底生出一丝冷意。
来了,这才是皇帝召她入宫的真正缘由。真以为皇帝只是想看她和青禾绣的《傲雪红梅》吗?
皇帝什麽新鲜没见过,又怎会在意这些?不过是借着这个由头,把她们圈进宫里,为天家所用罢了。
*
杨知意心中微动,随含笑应道,“陛下圣明,臣女所思,亦在此节。臣女今入尚服局,愿倾力研制新染料丶新织物,自当先供陛下丶娘娘及宫中贵人御用。”
“天家御用,自是人间至珍,非寻常所能比拟。而宫中所兴之风,素为民间仿效。若世人得知某色某纹为皇上与皇後所喜,必趋之若鹜,争相效之。”
“是以,宫廷既保尊贵之姿,民间亦得一丝馀泽,此乃‘与民同乐’之仁政;同时又能刺激民间织造,使其技艺精进,货物流通,税赋亦随之增长。天下财富汇聚,国力方能日益强盛。”
这番话,既捧了皇帝“与民同乐”的圣君形象,又点明了实际的经济利益和皇权彰显,更巧妙地将自己的私心——获得宫中优越的资源,潜心研发;同时将技艺得以推展流播,借此带动天下女子提升技艺与地位——包裹其中。
她语气从容,举止得体,言语间不显一分私心。
皇帝听罢,龙颜微展,似觉大有所得。少顷,方含笑道,“杨氏所言,正合朕意。”
“汝心怀社稷,识大体丶明轻重,实属可贵。朕便允你便宜行事,尚服局渚务,汝可酌情调用。暂封正八品采章,望你不负朕望,早出佳绩。”
“臣女谨遵圣谕,不负圣恩。”
林青禾跟着杨知意一起跪拜。她音落如清泉入石。
御书房外风过帘动,云光倾斜。
*
两人出了御书房,只觉得日色依旧,阳光暖人。宫墙上秋影轻颤,似无一丝异样。两人都出了一身冷汗。
林青禾怔怔站在檐下,过了一瞬,忽地伏在杨知意肩上,小声啜泣,“知意姐姐……宫里怎麽这样可怕?我方才……方才要站不住了。”
她声音哽咽,几乎带着委屈与惶然,“我们在苏州时,还都想着要入宫当绣娘,想着那是光鲜体面,如今才晓得,原来……宫中竟这般压人气息,一句话都不敢多说,连呼吸都觉得不敢太重……”
杨知意低头望她,伸手轻抚她背脊,柔声道,“宫中自有宫中的规矩,若有成事,便要习惯这份沉重……青禾,你怕不怕?”
林青禾擡头望她,见她神色温和,却透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坚韧,不由得怔了怔。接着便伸手擦干自己的脸颊,抱着杨知意,“有知意姐姐在,我就不怕。”
杨知意轻轻一笑,未答话,擡头望天,只见宫墙之上,秋日光华铺洒如织。
*
与此同时,齐砚回京後,其身世方才宣露——竟是当今圣上的外甥,安国公府的世子。
他一心记挂着杨知意,数次欲向母亲提及求娶之意,均被母亲以“门户不当”严词驳回。
齐母道,“我儿糊涂!那杨氏不过一小小采章,纵有些技艺,给你做妾已是擡举,你竟妄想娶为正妻?你是不想要我安国公府的脸面了?”言罢,更为积极地为齐砚张罗门当户对的亲事。
齐砚性格外和内刚,不愿因此与母亲决裂,却也不想妥协。他心知杨知意身在宫中,终非一朝一夕可得,遂托言“专志仕途,为国效力”,婉拒诸多婚事。
为避家中纷扰,亦为将来有力庇护心上人,他主动请缨,弃袭家荫,再应科举,得中後,进入工部,主动请缨外放,从水利丶营造等实务做起。
数年间,他奔波大江南北,勘测水利,督修河堤,参与城建,政声斐然,也磨砺得更加沉稳干练。
然,虽身处万里,心却未尝远离。两人书信传语,互道平安,互通心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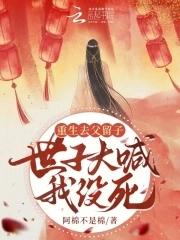

![顾少是怎么变渣的?[重生]+番外](/img/3301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