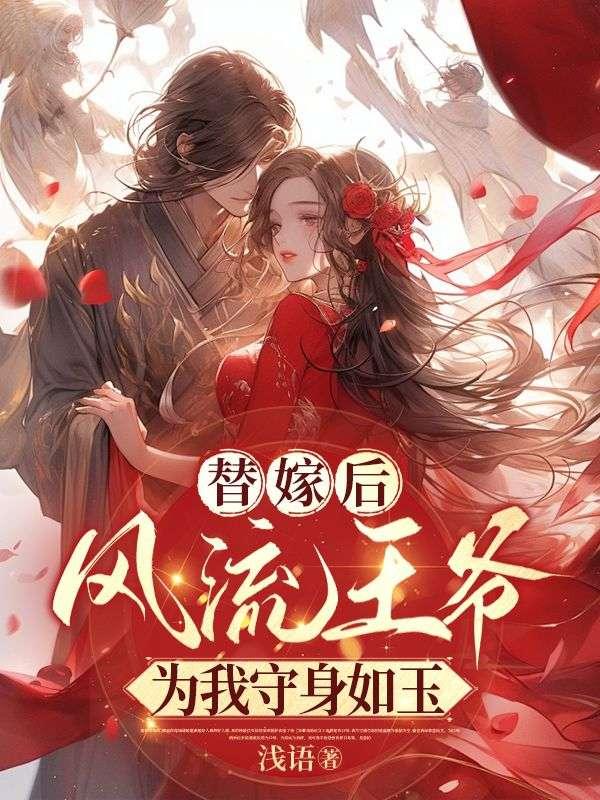富士小说>假千金她回家种田了红甘泉 > 第24章(第1页)
第24章(第1页)
到了晚上,老村长把大家召集在一处,将此事一说,果不其然大家都十分赞同。
还有很多青壮男子自告奋勇,修旧宅改建成学堂。
赵明笙想按市面上价钱来给他们发工钱,却被拒绝了。
一个皮肤黑里透红的大叔爽朗笑笑,说道:“左右不过出几天的苦力,东西都是现成的。不用给工钱。”他挠了挠后脑勺,有些憨厚地又犹豫地问:“俺们不要工钱,能不能到时候少收一点学费”
憨厚中带着一点卑微,但都全然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在外打拼苦累也一力承担,这样的父亲在村里不占少数。他问出了大部分人的心声。场面有一瞬间的沉默,沉默的让人心疼。
“大叔你放心,村里这个学堂是免费的,老师我也找好了。”赵明笙向大伙解释道,“这个学堂只是为了启蒙大家,教大家读书写字,多点知识将来也多条出路。”
话说明白了,那些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脸上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
一位穿着灰色衣裳的大娘,犹豫了许久,最后为了自己孩子硬着头皮问道:“我家娃今年十二了,不知道学堂还收不收”
有钱富贵人家三岁便开始启蒙,普通学堂最迟也六七岁就该启蒙,自家孩子岁数大,她害怕学堂不收。
她身边站着个半大的男孩,听到母亲询问忍不住扯了扯她的袖口。
“娘,别问了。肯定不收的,哪有像我这么大才开始启蒙的。”这话一出口,他的脸上也泛起落寞之色。
赵明笙认得那个男孩,是经常来给赵家送羊奶的石小子,八岁那年他父亲去世,家里就剩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穷人家孩子早当家,母亲又体弱多病,当时还年幼的他不得不担起家庭的重担,自然错过了上学的机会。
“大娘,不限年纪。”赵明笙保证道,“就是您这个年纪来学,学堂的大门也为你敞开。”
大娘激动地涨红了脸,她说:“我家娃能来上学就好,我就算了”
旁边的妇人也跟着七嘴八舌道:
“我们都一把年纪了,这不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吗!
“就是就是,能让孩子们去上学我们就很满意了!”
话糙理不糙,赵明笙被这些俗话弄地哭笑不得。但她还是坚持道:“只要想学,什么时候学都不晚。学堂收人不限年纪,不限男女。”
她的这番肺腑,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大家都安了心,当即就给自家孩子都报上名。
那些懂建房的汉子,自发地从当天晚上就开始干活。
木材石料都是从山里弄来的,泥沙从河底挖。
用新鲜好木头替换老宅子已经腐朽的老木头,再用土窑烧制土砖,青山村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建房子。
大家都一致不要工钱,赵明笙也只好作罢。只每到饭点的时候,和邹大娘一起做好了大锅饭给他们送去。
平常逢年过节才有点荤腥,到了这里顿顿有肉,一个个大快朵颐,吃完饭更有干劲了。
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建房搭得快。不出三天,就将老旧宅子焕然一新。
原本低矮破旧的草垛房子,改造成了高大宽敞的木头房子。为了方便孩子们读书,还特地多开了几扇窗,这样采光会更好。
以王木匠为首的木工还上山砍了些竹子,给孩子们做课桌椅,边边角角都磨得光滑,保证不会伤到孩子,
崭新的竹制桌椅,整齐地摆放在亮堂的学堂里。看着空空地桌面,赵明笙总觉得缺了什么,她一拍脑袋,终于想起了缺了什么。
笔墨纸砚。
赵明笙准备去镇上采购一些笔墨纸砚等学习用具。顺便把剩余的七宝美髯丸,和炮制好的药材拿去镇上看看能不能卖出去。
这几天,赵明笙一边忙着学堂的事,一边还忙着炼制七宝美髯丸,还真让她捣腾出来了。
赵父对她炼制的药丸也给予了充分地肯定。还给赵母服用了两天,她两鬓的霜白不出三天就有了乌黑的迹象。
赵明笙从中看到了商机。
赵明笙刚收拾好准备出门,正巧赵清越今天旬假,放一天假,便跟着一起来了。
镇子上人头攒动,小商小贩络绎不绝,好不热闹。赵明笙好久没见过这般热闹,看什么都新鲜的不行。她在一首饰摊子前驻足,红绸布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发簪耳饰,虽然比不上京城的样式,但是胜在精巧。
她随手挑了一根木簪,在头上比划。
小贩看着有戏,便鼓吹道:“小娘子真有眼光!这可是吴大师的手艺!五两银子给你,旁人我还不卖这个价格呢。”
赵明笙正准备放下,听到这句话手微微一顿。
当今世上工匠级别能被称作大师的人寥寥无几,笼统算下来不超过八人,这吴大师便是其中一人。
他擅长木雕,一朵莲花,别人能雕刻出八瓣就已经顶了天,他能凭借精湛的手艺雕刻出十二瓣。
这要真是吴大师的作品,五两银子还真不贵。
“喜欢的话便买,哥哥这里有钱。”赵清越不知什么时候跟了上来,刚好听见小贩这句话。
赵明笙按住了他正在掏钱袋的手,转身对小贩说道:“这吴大师的作品我也有幸得过一件。”她说的漫不经心,说完还不忘去瞧那小贩脸上的神态。
果然,一听说她有吴大师的作品,小贩神情立马慌张了起来。但是他忍不死心,继续嘴硬道:“你看,这上头的莲花足足有十二瓣嘞!这样吧,二两!二两银子你拿走。”
“我记得吴大师曾说过一句话,世上没有两片脉络一模一样的叶子,花也一样。”赵明笙一字一句道,“他手下的花瓣,或是残缺或是朝向不同,总之从来没有两瓣是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