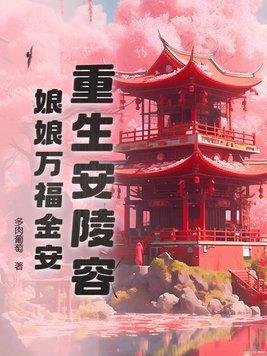富士小说>我循着光照的方向 > 第15章(第1页)
第15章(第1页)
“有时候我觉得离这个世界挺远的。”她笑了笑,“可能因为是水瓶座吧。”
“又是星座。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很信,真的准吗,所有的人就分成那么十来种吗?”
“上帝要造那么多的人,总是要给他们编个号,分一分类吧。”她说,“就像图书馆里的书,每一本都和其他的不同,但是它们也会被分类和编号。这样想要哪本书的时候,才能很快找到,而且再添新书的时候,也比较容易避免重复。”
“你真厉害,”他说,“让上帝变成了一个图书管理员。”
“我只是打个比方……”她连忙解释,很怕被他认为是亵渎神明。
在她的想象里,作家都有坚定的信仰。
侍应把主菜端上来了。牛肉和鳕鱼看起来让人很有食欲,他们切成几块,与对方交换。她觉得应该问他一些问题,可是她对文学了解得实在太少了。
“你写作的时候,是不是需要特别安静的环境,与世隔绝的那种?”她问。
“年轻的时候是这样,总想躲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写作。”
“现在呢?”
“现在愿意待在热闹的地方,每天会会朋友、喝点酒。”
“人年纪大了,不是应该喜欢清净吗?”
“可能还不够老吧。不过没准儿越老越爱热闹,”他笑了笑,“我只是说我自己啊,别的作家可能不这样。”
“我只认识你一个作家。你什么样,我就觉得他们也什么样。”她说。
“那我可要表现得好一点。”他说。
她笑起来。但他没笑。
“有时候想一想,多写一本书,少写一本书,有什么区别呢,也就这样了。真是没有当初的野心了。”他有些悲凉地望着外面的湖。
过了一会儿他转过头来:“我想起了一点往事,想听吗?”
“当然。”
“写第一部长篇的时候,我儿子刚出生,家里房子小,为了图清净,我到乡下住了几个月。那地方很荒凉,只有几幢空房子,据说是风水不好,人都搬走了。我就在那里写小说,傍晚到最近的村子里吃饭。有一天喝了酒,回来的时候一脚踩空,从山坡上滚下去了。当时醉得厉害,就在那里睡着了。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大石头上,面前是一片茫茫的大湖。像极了聊斋故事,一觉醒来什么都不见了。我当时没想到老婆孩子,第一个反应是,我那个写到一半的小说呢?它是不是一场虚幻,其实根本不存在?”
他怔怔地坐在那里,好像等着自己从故事里慢慢出来。侍应走过来,拿走了面前的盘子。
“那个时候,我也许是一个称职的作家。”他说。
两个中年男人从外面进来,皮鞋上的雪震落到地板上。壁炉在角落里吱吱地摇着火苗。邻桌的情侣沉默地看着菜单。
“我知道你说的那种感觉。”隔了一会儿,她说。
很多时候,她也感觉自己是在一个梦里。璐璐没有死,因为她并不存在。小松一家也不存在,她根本从未到美国来。这一切都是梦,梦像一条长长的隧道,穿过去就可以了。
去洗手间的时候,她沿着一条木头地板之间的缝隙,想试试自己还能不能走直线。镜子里的自己,嘴唇被葡萄酒染成黑紫色,像是中了剧毒。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小松的名字在屏幕上闪烁。她伸手按掉了它,感觉到一丝快意。
夏晖提出再到酒吧喝一杯,她想也没想就说好。需要点锋利的东西,把梦划开一道口子,然后就可以醒过来了。
推开餐馆的门,冷空气吹散了脸上的酒精。心像一个攥着的拳头,慢慢地松开了。
“我们走到湖上去吧。”她转过身恋恋不舍地说。
“滑冰吗?”
“就想在上面站一下,你不觉得它就像一块没有人到过的陆地吗?”
“别傻了,冰一踩就碎了。”他说。
几个美丽的少女站在大街上,寒风镂刻出雕塑般的五官,幽蓝色的眼影在空中划出一簇磷火。一个女孩走上来问程琤要烟,她耸耸眉毛,为自己未满十八岁感到无奈。程琤递给她一支烟,按下打火机,用手挡住风。女孩把烟含在两片薄唇之间,偏着头凑近火焰。她闻到女孩身上甜橙味的香水。
另外几个女孩也走过来,对着他们微笑。她把那包所剩不多的万宝路送给了她们。
“我看到这些女孩,就会很难过。”她看着她们的背影说。
“为什么?”
“我觉得自己老了,而且好像从来都没有年轻过。”
“小丫头,你这才走到哪里啊?路还长着呢。”他伸过手来,拍了拍她的头。她的眼圈一下红了。
从湖边的餐厅来到酒吧,如同从云端堕入尘世。暧昧的光线融化了头发上的雪花,冬天的肃穆淹没在轻佻的音乐里。人们叫嚷着,好像谁跟谁都很亲密。他们坐在那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大衣搭在椅子上,口袋里的手机在她的背后震动,像一颗就要跳出来的心脏。她有一点同情小松。
夏晖比画着问侍应又要了一瓶酒。
“你明天还要赶飞机呢。”
“没关系。”他看着她,像是在说他们有的是时间。
“你知道吗,”她把刚倒上的酒一饮而尽,“我有一个朋友很崇拜你,读过你所有的书。”
“是吗?”他笑了一下,似乎已经司空见惯。
她摇着杯子悲伤地说:“本来来的应该是她。可我呢,我从来没有读过你的书,我对你一无所知。”
“这不是很好吗?”他说,“没有东西隔在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