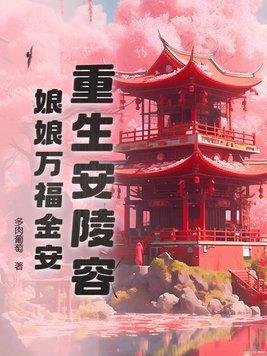富士小说>我循着光照的方向 > 第49章(第1页)
第49章(第1页)
还要在茶几上漫不经心地丢几本书,以示她热爱阅读,并且好像不是专门在等着他来。
美式咖啡续了两杯,又吃掉一个马芬蛋糕。收到母亲的一个短信,她终于妥协,不再打电话来。只是告诉绢明早起床后,记得把锅里配好原料的“甜甜蜜蜜”羹煮上。又嘱咐她晚上一定要早睡。八点半,欧枫才打电话让她上来。
绢一进去,欧枫就把门反锁上。关掉所有的灯,抱住了她。她很气恼,因为他甚至没有来得及看清她身上的裙子。他的手已经摸到背后的拉链,一径到底,把她剥了出来。黑暗中,听到另一道拉链的声响,然后她就感到那个家伙拼命顶进去。在这一过程中,她再度变成一个绵软的木偶,失去知觉,悉听尊便。她想起下午和乔其纱讨论的有关避孕套的问题,觉得非常可悲。每一次,她被男人剥光的时候,大脑都是一片空白,好像死了过去,没办法发出声音,或者做任何动作。所以她从来没有打断男人的进攻,要求戴一枚避孕套。究其原因,也许应当再次追溯到在多伦多的时候,最初的两年,她看着乔其纱不断更换男友,和他们出去过夜,可她还是个纯洁的处女。在这样的年代,纯洁真是一个具有侮辱性的词语,它暗示着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因而无人问津。她觉得自己就像货架上的积压货,落满了尘埃。
那一时期的压抑和匮乏,使她后来对性爱变得盲目渴望。没有避孕套没关系,没有快感没关系,没有爱也没有关系。她就好像一个荒闲太久的宅院,只盼着有人可以登门造访。虽然明知道,有些人只是进来歇歇脚。
但欧枫不一样。他和之前的那些人不一样。他不是进来歇脚的,也许最初是,但后来他长期留下来,做了这里的主人。当然,他并不了解这座宅院的历史,以为来过这里的人,屈指可数。绢给男人的感觉是,矜持而羞涩,属于清白本分的那类女孩。不过绢和欧枫在一起之后,的确变得清白而本分。本质上她并不淫乱,只是空虚。欧枫的出现,填补了这种空虚。取而代之的是等待。当然,等待最终兑换到的是另一种空虚,不过它被花花绿绿的承诺遮蔽着,等绢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这个男人是世界上给她承诺最多的人,恐怕以后也不会有人超过他了。也许他天生喜欢承诺,不过绢更愿意相信,还是因为他在意她,为了笼络她的心,必须不断承诺。他承诺过年的时候陪她去郊外放烟火,承诺带她去欧洲旅行,承诺离婚,承诺和她结婚,承诺和她生个孩子。放烟火的承诺说了两年,没有兑现。其他的承诺,期限都是开放的,如果她肯耐心去等,也许有的可以兑现。因为他也有兑现了的承诺,比如送给她一只小狗。于是变成了她一边和小狗玩,一边等。小狗死后,她开始养猫,一边给猫梳毛,一边继续等。他承诺的很多,但实际见面的时间却非常少。每次也很短,短得只够做一次爱。回顾他们的交往,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做爱,它们彼此之间那么雷同,到了最后变得有些程式化。
在某次做爱之后,欧枫疲倦地睡着了。绢钻出棉被,支起身子点了支烟,静默地看着他。他每次做完爱,都出一身虚汗,裸在被子外面散热。他身上总是很烫,抱着她的时候非常温暖。她要的就是这一点温暖,如果没有,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越冬。日辉从没有合紧的窗帘中照射进来,落在他的肚皮和大腿上。一直以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很黑,没有光线,她好像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把他的样子看清楚。她专注地看着他。他的皮肤那样白,也许与雄性激素的减少有关。翻身的时候,皮肤颤得厉害,像是树枝上就要被震落的雪。
你难道不觉得中年男人身上,有一股腐朽的味道吗?乔其纱的话又冒出来了。
此刻,她真切地感到了腐朽的味道。眼前的这个男人已经没有能力推翻现在的生活,重建一次。
绢终于下了决心离开。
青杨看起来很呆,做起爱来像一只啄木鸟,可是他还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时间和她一起变白。原来生命力是那么重要,唯有它,可以用来和孤独对抗。
绢躺在办公室冰冷的地板上,感觉到欧枫渐弱的痉挛。她发现喉咙很疼,刚才肯定又叫得很大声。他正要从里面离开的时候,她忽然伸出手臂,紧紧搂住了他的脖子:在里面多待一会儿吧。他就没有动,仍旧伏在她的身上。绢又说,你别睡过去,我们说说话吧。欧枫喘着气说,好啊。
你爱我吗?绢问。她很少这样发问。但是这句话,作为一场无中生有的谈话的开端,确实再合适不过。
当然。
你爱我什么呢?
你又年轻又漂亮,还很懂事。
哦。绢轻轻地应了一声,说,比我年轻比我漂亮的女孩有很多,她们也会很懂事。
可我不认识她们,我只认识你。我们认识就是一种缘分。
绢没有说话。这个答案真是令她失望。他不爱她们,只是因为不认识。
他已经完全从她身体里退出来,在上面有些待不住了,做爱之后,男人会本能地想要脱离女人,似乎对刚才的依赖感到很羞耻。她箍紧手臂,不让他动,带我走吧,和我一起生活。别眼睁睁地看着我嫁给别人,好吗?绢伏在他的肩上,滚烫的眼泪涌出来。这一刻的感情如此真挚,不是爱,又是什么呢?绢好像也才刚刚明白自己的心迹。她还是舍不得他,纵使她虚荣,害怕孤独,可现在如果他答应,她可以把这些都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