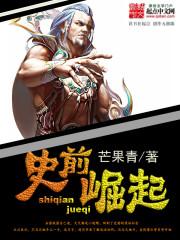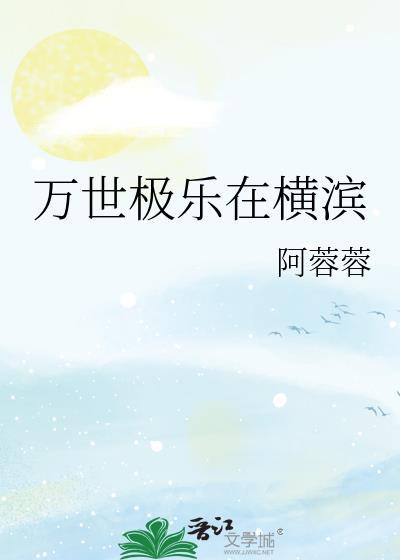富士小说>师父不可以(限)洛灵犀笔趣阁无弹窗 > 第31章(第1页)
第31章(第1页)
前来禀报的衙役神色亦慌,他一动不动地站在下,等着县令大人号施令,却久不见上座的大人有所动静,这让他不禁抬头看了看赵秉烛。
只见赵秉烛目光呆滞的靠在太师椅上,脸上六神无主,一幅被吓呆住了的样子。
“大人?”衙役出声唤道,额上也冒出些冷汗。
疫病有多可怕,他自然知道。
前朝时,有一个郡突疫病,因郡守懈怠,没及时管控,一不可收拾,造成扩散传染至诸多地域,死了近万人。
十年前,昭武太子谢怀襟,率领三万大军平叛西南道。胜利归途,其突疫病,传染诸多将众,皆殒命道中。
被这声呼唤叫过神,赵秉烛连忙问:“你方才说是什么人来报的信?”
方才,他只听时疫二字就已慌了神,听完这起时疫患者的症状,之后衙役说的话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衙役开口复述了一遍:“回禀大人,是青灯镇的镇长和道观内的一个叫悟清明的道士,据他所言,现的第一个患者是青灯镇书院的夫子,已经让其及家属暂避家中,不可外出与其他人接触。”
“噢,初步管控的甚好,甚好!”赵秉烛举袖擦了擦额上细汗,“那个悟什么道长,此人还在吗?”
他此前好像从女儿口中,听过这个名字,似乎很受女子青睐。
那会他只当是个油头粉面,不怀好意的妖道,因此还禁了闺女的足,不让她去青灯观上香。为此,闺女好长一段时间不曾理过自己。
“悟清明在外候着。”衙役抱拳道。
“快把他们叫进来,本官要多了解些情况。”
“是。”衙役俯身一拜,赶忙出去将悟清明召唤进来。
赵秉烛从椅子上起身,坐立不安地在门口徘徊,不断哀声叹气。
少顷,他只见阳光之中,两道身影,一袭衣袂由远及近,逆着光线疾步而来。
临近了才看清,青灯镇镇长旁边的那位眉目祥和,额上系着一字道巾,身着霁青色道袍,脚下踏着十方鞋,一派雨过天青的清净出尘之态,宛如下凡救苦救难的神仙。
他停在自己前方三尺处,对着自己行了一礼:“贫道悟清明,见过年县令。”
赵秉烛忙上前一步:“清明道长有礼了,本官替镇中民众,谢过道长及时来报。”
悟清明摇了摇头,“贫道亦是镇中民众,此乃力所能及的事。”
“好,道长心系民生,我不妨就直接说了,”赵秉烛别的本事没有,看人却是一看一个准,也正是如此,当年安王袁营起事时,他才没有跟着上司投靠归顺,只装傻充愣。
之后天下果然还是谢氏的天下,那些个归顺袁贼的墙头草,此后陆续被当今圣上清算铲除。
不像他,经历山河飘摇,改朝换代,依旧不动如山。
当下,赵秉烛便觉得悟清明一身浩然正气,绝非那等坑蒙拐骗的江湖术士。
于是他开门见山,直接礼贤下士:“依您之见,这起时疫,接下来该当如何防范?”
悟清明没想到这父母官竟这般毫无主见,也不遮掩一二,遂也言简意赅说了自己的看法:
“要的事,即刻封锁望县城门,禁止人口流动,以免疫病扩散;其二,派遣人手前往青灯镇排查与孟夫子有所接触之人;其三,召集城中大夫,在青灯镇中开辟出专门的善堂,统一安置诊治感染者……”
“此外,还需追溯疫病源头,以便及时预防,对症治疗。”
悟清明将那日观中听得的所知情况悉数告知,与青灯镇一川之隔的白水镇,只怕就是源头所在。
赵秉烛逐一记下,命人封锁城门,连忙提笔写出告示,派遣衙役逐一送至各个镇长手中。
是夜,赵秉烛叹了口气,扯得嘴角一痛,他索性站起身来,一把换下官袍着了便装,准备出去走走。
刚开门,就差点和赵夫人撞了个满怀。
赵夫人端着茶碗被他这一撞,险些洒出水来。
赵秉烛急忙扶助她,待她站住脚跟,把茶往他身前一送:“天都黑了,这是要往哪去?给你煮了苦菊茶,清肺去火的,瞧瞧你这嘴角都急的长出燎泡了。”
“事多心烦,想出去透个气,”赵秉烛端起杯子,一口闷,不由皱着眉头,“苦的。”遂抬腿出门。
“回来,”赵夫人凝眉,重声一喝,“外边正闹疫病,你还出去做甚?”
赵秉烛踏出的一只脚,闻声又缩了回来,在屋中继续长吁短叹,愁眉不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