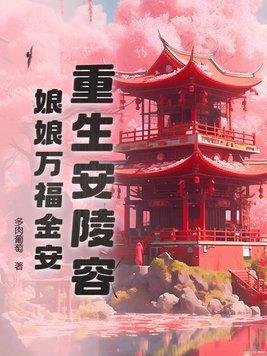富士小说>病美人被宿敌巧取豪夺后 > 第191章(第1页)
第191章(第1页)
“……嗯。”闻折柳发顶在她脸颊蹭了两下才松开,“你也要保重身体。”
“好。”
何霁月简短回答,将披风往肩上一盖,匆匆离去。
再不用强行支撑,无力到发抖的上半身,闻折柳任由身子软面般滑下,在床榻瘫成一团。
只是身子因无力而静,心却烦躁不堪。
非得将手臂掐出好几道血痕,才能勉强冷静下来。
当时她们一家入狱,他与生父如惊弓之鸟,不敢辩驳——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怎奈他们真与西越有勾结——仔细回想起来,他养母闻相……
倒是一副坦然赴死的模样。
好似早就知道这一日会来临。
可聊些家长里短的东西,顶多给闻相定私藏西越人的罪,此罪,真的至死么?
再者,何霁月现在愿意相信他,彻底查清楚当年闻氏一族入狱的真相,可是因为他这一身病气,以及他那动弹不得,只能委屈靠在床榻,日渐萎缩的双腿?
那……他的腿若能走,何霁月这悉心关照,岂不是也似镜中花,水中月,飘飘乎如凭虚御风,蒸腾而去?
不成。
闻折柳盯着自己无法动弹的腿,若有所思。
怎么才能让它彻底没法动呢?
砍掉,兴许可以。
连双腿都不存在,他腿上的筋脉,自然也就完全没有恢复之日了。
恰好何霁月去前头,与慕容锦商议,不在他身侧,又心绪烦乱,少说也要三刻才回得来。
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软枕下头,隐约有块凸起。
闻折柳伸手一探,熟稔摸出把匕首。
锋利寒光一照,刀面上,映出他嘴角那抹憔悴又苍凉的笑。
这匕首,是何霁月赠予他防身用的。
谁知道,居然被他用在这个地方。
借着帐篷里的烛光,闻折柳看清楚大腿根的位置,心一横,眼一闭,双手紧握匕首,刀尖向下,用力一刺……
“嗒”一声,茶杯放到慕容锦跟前。
“慕容……姑娘。”何霁月依旧只知她姓甚,记不清她名谁,索性将就这么叫。
“来者是客,喝茶。”
这慕容锦,是与闻折柳行过妻夫礼,还有“洞房花烛夜”的女子。
照理说,她是该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