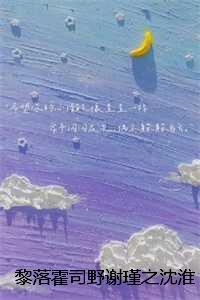富士小说>荒()离() > 耕读大事(第2页)
耕读大事(第2页)
识字,便是那一根火种。
她从一开始便在筹备村学,选址就在村中心祠堂一侧。墙面刷了新泥,窗纸糊得洁白,桌椅板凳都是林通带着几个年轻人亲手做的,虽不规整,但结实耐用。屋檐下挂了青铜风铃,门口立了三尺竹竿,上挂墨字布幡——“禾安学堂”。
字是孟阿翁所书,苍劲遒劲,一气呵成。
学堂开课那日,天刚放亮,村子便安静许多,村里老人早早为孩子梳好头发,换上干净衣裳。虽说衣衫褴褛,但那份郑重却是透骨的。
清晨第一课,是给十岁以下的孩子开蒙。
孟阿翁站在堂中,身着洗得泛白的直裰,胡须梳理得一丝不乱。他看着面前这一群或怯生丶或好奇丶或兴奋的孩子们,神情比以往更为温和。
“今日起,你们便是我禾安学堂的弟子。”
他一字一句,清晰有力。
接着教孩子们正身端坐丶执笔描字丶跟读口诀。
“天丶地丶人丶禾丶安……”
写到“禾安”二字时,有孩子小声问:“这是我们村的名字吗?”
孟阿翁点头:“是,也是你们的根。”
日上中天,村中最热闹的豆腐坊一带才稍稍安静下来。那一群每日清晨忙着打浆丶点卤丶卖豆花的半大小子与丫头此时匆匆赶来,在学堂外呼啦啦一阵换鞋入座,正是第二班——青少年识字课。
他们年纪不小,手也不巧,写字一时比小孩子还难些。
“笔直,慢写,不是赶着卖豆腐!”孟采薇在一旁提醒,像个小先生似的。
“嘿,你这小夫子凶得很。”孙冬生嘴角一抽。
“凶你才记得牢。”孟采薇笑着回。
一时间,学堂里满是笑声。
最不容易的,是中午和傍晚的“扫盲课”。
那是给全村最忙最累的那一群人准备的课,林青禾与孟阿翁商量,将时间错开,争取哪怕一日只有半个时辰,也得教他们识字。
林青禾没有太多要求:“自己的名字丶家人的名字丶禾安村的名字,能写清楚就好。还有种田丶养鸡丶做豆腐时常用的字,一定要认得。不然,咱自己记不了账,将来别人拿着账糊弄你,你都不知道。”
衆人听了都点头,可真轮到上课时,一个个却像做错事的孩子似的,连笔都握不稳。
“你叫啥?”孟阿翁问。
“赵芦花。”
“来,写‘赵’。”
赵芦花的手抖得厉害,半天才在纸上描出一个歪歪扭扭的字,跟蚯蚓似的。
孟阿翁不骂,抚须笑道。
“好得很,从今天起,你就认识自己了。”
赵芦花一听,眼圈红了。
她何曾想过,自己还能有一日,能写出自己的名字?
她出身贫苦,少年守寡,在逃荒路上几次以为命不久矣。如今坐在堂中,手握笔杆,写着“赵芦花”三个字,那感觉,就像是从黑夜走进了天光。
从村学开课起,孟阿翁便被衆人尊称“孟夫子”。
而他的“助教”,便是自家儿子孟听松丶儿媳李漱兰,还有孙女孟蘅芜与孟采薇。轮班授课,从未懈怠。
起初两位姑娘还有些不好意思,尤其是被村里的几个顽皮男孩喊“小夫子”时,总是脸红耳赤,恨不得躲回家中不再来教书。
可渐渐的,她们不再羞怯。
她们开始备课,开始纠正姿势,开始为哪个孩子学得慢而操心,也会为她们写出第一个完整的“林”字而偷偷欢喜。
她们不知道怎麽说出那种感觉——但她们知道,每天睁眼醒来,能教人识字,那一天便都是欢喜的。
暮色四合,学堂最後一班刚刚散去。
林青禾送来几盏灯油,与一大竹筐野果,说是慰劳先生和助教们。
她站在门口,看着灯光将学堂照得暖黄,听着屋内孟阿翁教孟采薇如何更正笔画,心中一阵宁静。
“这一年,我们走了很远的路。”她低声说。
“如今总算能让人停下来,种地丶读书丶活着。”
屋外虫鸣,星子微明,禾安村在静夜中沉入梦乡。
不久的将来,这些孩子会写字,会算账,会记住自家姓甚名谁,知道这个叫“禾安”的村庄,是他们落脚生根的地方。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 黎落霍司野谢瑾之沈淮川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结局+番外黎落霍司野谢瑾之沈淮川
- 放着一些东西。他们冲过去,瞬间心脏骤停。居然是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