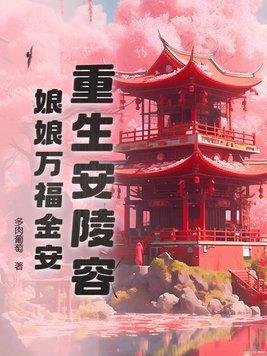富士小说>糙汉攻文推荐原耽文 > 第33章 C33 百达翡丽(第2页)
第33章 C33 百达翡丽(第2页)
张将看着他,心脏仿佛被什麽攥得死死的,一瞬间他感觉气血翻涌,王太太的话,丽虹姐对他的称呼,全都在脑子里串成线。
小沈总,沈辞洲。
-小沈总,我的合夥人
-
-那位风流的不得了的小沈总
-可惜是弯的
-我听说他玩得花得不行,好像还在申城艺术学院包了个艺术生
-啊?还包了体育生?
-
张将恍然,他早该知道的,早该猜到的,在床上那麽放得开,懂那麽多技巧,那麽会说花言巧语,怎麽可能是个善茬。
这段时间的相处就像是一场梦,每个抵死缠绵的夜,他以为是爱,以为是喜欢,以为是心动结果到头来获得“炮。友”二字,他对他说的话不知道是对多少人说过的二手情话。
原谅比被绿了,更痛彻心扉的是他根本就没有被绿的资格,他只是无名无分的炮。友。
他是个笑话,彻头彻尾的笑话。
被一个从申城来的浪荡子玩得团团转,把所有积蓄都玩进去,把一颗心都玩得破碎不堪,把自己玩得快要疯掉。
“我们只是炮。友”张将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像是冻住一般。
沈辞洲看见他眼里的红血丝和绝望感到有一丝痛快:“不止。”
张将眼睛微微放大,就听见沈辞洲继续说,“说得好听是炮。友说得难听点,你不过是我一时感兴趣的人形按。摩棒罢了,只不过这个按。摩棒贵了点,价值一块百达翡丽。”
张将听着他一字一句,心口像是被剜去了一块,原来极致的痛苦是完全没有办法发出声音,他的心仿佛被倒满了玻璃碎渣,每呼吸一口都痛得快要死去,他张了张嘴,什麽也说不出来,沈辞洲顺势把他从门口推开,开门之前还不忘又踹了他一脚,骂了句,“死捞男。”
张将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意识有些模糊,他扶着门,头脑一片空白,心脏忽然绞痛起来,嘴里血腥味浓重,分不清是刚刚被打的一拳,还是气血攻心,他失去力气整个人跌坐在地上,眼里的光在一瞬间熄灭,只剩一片死寂的灰烬。
原来都是他自作多情。
原来都是假的。
他曾经认真想过要好好努力,要好好挣钱,要让沈辞洲一直可以住在一万多一晚的房间,不能让沈辞洲跟着他吃苦,他设想过他们无数的未来,结果到头不过是他一场空梦。
他以为沈辞洲说喜欢他是真的喜欢他,他以为沈辞洲和他睡了就是他的人,却在现在才知道那些话并不是专属于他。
他曾以为上帝眷恋他,在他死去的若干年後把沈辞洲送到他面前,给他生活一丝光,他把所有的真心所有的热忱都献给他,可到头来不过是沈辞洲的一句“人形按。摩棒”,连人都算不上,他的人格丶自尊被彻底踩碎,他的存在是一个死物,一个供他享乐消遣的情。爱玩具。
王丽虹看他脸色差到极致:“小张,怎麽了?”
张将失魂落魄,可他不能请假回家,丽虹姐对他这麽好,他怎麽能在开业没多久就请假,就算请假,他还有一堆事情要处理,他的爸爸躺在那条冰冷的河里整整十年,他还要替爸爸找回公道,他不能倒下,不能因为沈辞洲那个烂。裤。裆的浪荡子倒下,他可以绝望,但决不能是现在,他得撑下去,他要撑下去。
“没事,丽虹姐,我先去忙了。”张将说话都感觉五脏六腑在疼。
“你脸肿了?真没事吗?”
张将摇头:“没事,刚刚不小心撞的。”
王丽虹最终没有多问。
张将走了一步,折回来问道:“丽虹姐,你知道百达翡丽吗?”
“知道,怎麽了?”
“是什麽?”
“手表。”
“很贵吗?”
“不便宜。”
张将想不明白为什麽沈辞洲说他拿了他的表,他的表,他脑子对手表完全没有印象,王丽虹伸出手,腕上是一块翡翠绿的手表。
“正是赶巧,我刚好今天戴了。”
雪山白的表盘,简洁布局,表圈镶嵌着碎钻,张将忽然脑子里闪过一款墨绿色的表盘的表,沈辞洲来按摩店第一天手腕上带的表,当时因为要按摩,脱下来放在按摩床的搁置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