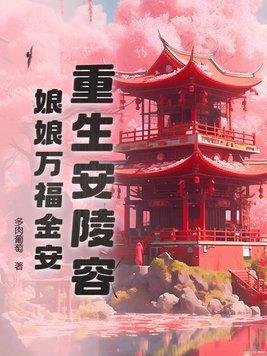富士小说>情生贱骨免费阅读 > 第7章(第2页)
第7章(第2页)
他侧身躲闪,露出背後宦人,背後宦人拔刀,挡下飞来的刀刃。
“你看,我就说印蕴没仔细查女刀客的案子,”梁去华伸手拉背後宦人的小臂,“边悯,别怕,她不敢继续来。”
边悯嫌弃抽手,抽不出来,只好擡头看一圈,刚擡头,人影闪到面前,利刃直砍他二人接触的手与腕。
梁去华放手,往後退两步,刀锋立转,斩他胸腹,传来剧痛,他目光所及是雨笠与白纱,胸腹再次吃痛,人向後仰。
他被一脚踹下山道。
边悯下意识往前走一步,但梁去华掉下去得很快,他还没来得及伸手,被扇了脸,栽在地上,雨泥溅满身。
“梁去华这个贱人。”
人刚要跳下去追,被边悯扯住袖子,“印蕴,别追,是埋伏。”
印蕴踹开边悯,“不是你把他行踪透给我的?”
“他把我也算计了,”边悯仰脑袋,雨打进眼睛里,睁不开,朦朦胧胧里看见印蕴神情骇人,不知是雨淋在身上冷,还是气氛太冷,他微微发起颤。
印蕴眨了眨眼,“那你也滚下去好了。”语罢,又是一脚给边悯也踹下山道。
东厂院子死寂一片,忽然有番役跑过来开门,“快去请医,梁掌印受伤了!”
院子里点起油灯,雨淅淅沥沥,闹腾到四更,梁去华的值房才熄灯,熄灯不久,边悯出来了,一路出东厂,回私宅。
刚推开寝屋门,边悯还没来得及换下湿衣,叫人掐住脖子往地上摁,他越挣扎,掐得越使劲。
“你最好老实说今晚到底怎麽了,”清细的声嗓裹着威胁。
“我说我说,”边悯不挣扎了,挣扎也没用,索性胡乱摸索,摸到他双臂,“印蕴,你先放开我,要喘不上了。”
印蕴哼声起身,踹他一脚,“起来吧。”
湿衣紧贴皮肤,黏湿难受,边悯苦着脸跪地上,“行程确实是对的,梁去华今晚要去寺庙查旧迹,可是你来那会儿,他突然没有征兆地提起你办案,我想是他故意的,等着看女刀客究竟和你什麽干系。”
边悯也被踢下去了,那他就知道下面到底有没有埋伏,印蕴慢慢看向他,他肯定点头,“有很多番役等着,看我也被踹下来,迟迟不见人追,梁去华又伤得重,就撤了。”
要是印蕴追下去,没办法以一敌多,很可能被梁去华阴一手,当场把她捉了。
边悯说完,很难继续开口,印蕴打起人来不收力,那一脚踹得边悯到现在都缓不上去,喘息急促短暂。
虽然难受,但边悯还是很自觉地把脸擡起来,侧一个角度,好让印蕴打他。
印蕴没有打他。
她给他拍拍背,无意发觉他鼻息湿冷。
印蕴不阴不阳嘲讽,“真金贵。”
“你怎麽到我私宅来了?”边悯问,“我没有被糟践,你别杀我。”
“你这蠢物,既然都发现被梁去华算计了,还不能想到他今儿会查我行踪吗?我跟陈放说去寻欢,今晚宿你私宅,”印蕴推他一把,“滚去换衣裳,别脏了我手,我等会再找你算账。”
边悯垂搭眼皮,低头进浴房。
他知道印蕴要和他算什麽账。
擦干头发才回寝屋,边悯起先没找到印蕴在哪,于是拨开床幔。
印蕴半躺在榻上,边悯一回来,印蕴就勾手。
人是被扯到床幔里的。
印蕴侧了个身子,斜着半躺在边悯身边,“多久不见了?”
边悯不自在地挪动,叫印蕴按住,他扭头答:“一个多月吧。”
“那看来我没记错,”印蕴每一次动作,身上宽松的寝衣就摩挲出声,边悯後知後觉,印蕴换了衣裳,穿的他的寝衣。
他慌乱起来,眼神在雪白的寝衣和印蕴的脸来回游动,印蕴捂他嘴,懒得说寝衣的事,她坚持自己的话头,“今儿你生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