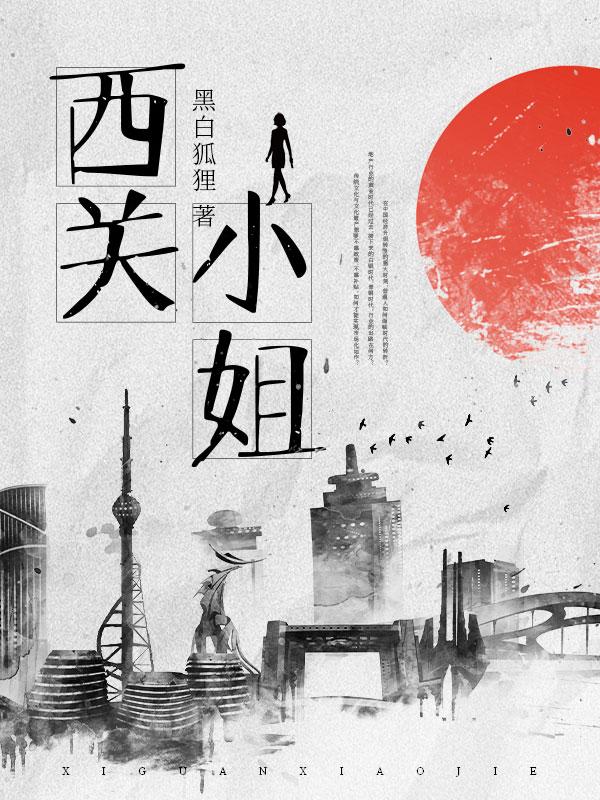富士小说>刘亦菲乒乓球 > 第8章 父母的理解与支持(第1页)
第8章 父母的理解与支持(第1页)
八一队训练基地的第一个夜晚,屈正阳在陌生的床铺上辗转。并非因为床铺不适——这里的条件远比青槐巷的老屋优越。而是一种混杂着兴奋、紧张与巨大压力的情绪,在他体内奔流,让前世历经风雨的灵魂也难以立刻平静。
他拿出手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爸,妈,我到了,安顿好了。”他的声音透过电波,努力维持着平稳。
“正阳!”母亲李慧兰的声音立刻传来,带着难以掩饰的关切,“怎么样?累不累?教练凶不凶?室友好处吗?”
“都挺好。王教练看起来严格,但讲道理。室友是樊振东,就是王教练提过的那个天才,人很热情。”屈正阳言简意赅地汇报,避重就轻。
父亲屈建国接过电话,语气一如既往的沉稳,却也能听出深处的牵挂:“到了就好。记住,多看,多听,多学,少说。专业队不同家里,一切靠自己。”
“我明白,爸。”屈正阳应道。短暂的沉默后,他轻声说:“你们也早点休息。”
挂断电话,宿舍里已响起樊振东轻微的鼾声。屈正阳躺在黑暗中,望着天花板,清晰地意识到,安逸的过去已被彻底割舍,他正站在一个全新世界的门槛上。
清晨五点五十,尖锐的哨声如同军令,撕裂了基地的宁静。
“快!十分钟内操场集合!”樊振东如同条件反射般弹起,动作麻利地套着运动服。
屈正阳不敢怠慢,用最快的度整理完毕,跟着樊振东冲向操场。晨曦微露中,数百名运动员已列队完毕,鸦雀无声,只有教练冰冷的目光扫视全场。
“晨练,五公里越野,最后一百名加练五组四百米冲刺!”教练的声音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命令下达,队伍如同开闸的洪流涌出基地。屈正阳调整着呼吸,试图将形意拳的桩功呼吸法融入跑步节奏。然而,专业运动员的配和耐力远他的想象。前三公里尚能勉强跟上,到了第四公里,肺部如同风箱般剧烈抽动,双腿灌铅般沉重,眼前阵阵黑。
“调整呼吸!步幅缩小,频率加快!别掉队!”樊振东不知何时放慢度,跑在他身侧,低声提醒。
屈正阳咬紧牙关,凭借着前世磨练出的惊人意志力,硬生生吊在队伍的中后段,冲过了终点线。他双手撑着膝盖,大汗淋漓,几乎虚脱,而身边不少队员只是微微气喘。
“可以啊,第一次跟操就能跑完,没趴下。”樊振东递过一瓶水,眼中带着一丝认可,“很多试训生第一关就栽了。”
上午的技术训练,强度再次升级。多球练习,教练站在球台对面,左右开弓,球如连珠炮般砸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高质量回球,落点、旋转、力量缺一不可。
屈正阳引以为傲的力技巧,在这种极限压迫下,也开始变形。手臂肌肉因乳酸堆积而酸痛颤抖,注意力因体能透支而难以集中。
“屈正阳!手腕放松!用身体带!你的‘巧劲’呢?被狗吃了吗?!”王建军教练的呵斥如同鞭子,抽打在他的耳膜上。没有因为他是新人而有丝毫客气。
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身体的抗议,脑海中观想起形意拳“三体式”的沉稳,努力将涣散的力量重新整合、传导。几个回合后,那独特的、兼具穿透与控制的击球感,才逐渐回归。
午餐时间,他几乎是拖着身体走进食堂。盘子里的营养餐色香味俱全,他却累得几乎拿不稳筷子。
“习惯就好。”樊振东坐在他对面,大口吃着鸡胸肉,“王教练说过,进了八一队,先学的不是打球,是当兵。这里淘汰的,八成不是技术不行,是精神先垮了。”
屈正阳默默点头,将食物机械地塞进嘴里。他第一次如此真切地体会到,业余与专业之间,那一道看似无形、实则坚不可摧的壁垒。
下午是战术合练和双打配对。王建军有意将他与樊振东编为一组。樊振东的正手重炮火力全开,屈正阳则凭借其诡异的节奏、精准的落点和匪夷所思的防守覆盖进行策应。
“好球!”樊振东打出一板漂亮的得分球后,兴奋地回头,“你这球顶得真稳!角度还这么刁!”
屈正阳笑了笑,汗水顺着下颌线滴落。他能感觉到,在适应了初步的体能极限后,他融合国术的独特球风,开始在这片更高的平台上,重新焕出光彩。一些老队员看向他的目光,也从最初的好奇,渐渐多了几分审视与凝重。
训练结束的哨声响起时,屈正阳感觉身体每一寸肌肉都在呻吟。回到宿舍,他连拿手机的力气都快没有了。简短给家里报了平安后,他瘫倒在床上。
“这就顶不住了?”樊振东一边做着放松拉伸,一边调侃,“后面还有夜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