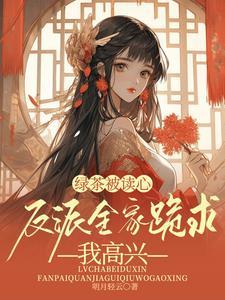富士小说>扶苏穿成宋仁宗太子喃喃果笔趣阁 > 125130(第7页)
125130(第7页)
因为第一世的惨剧,扶苏第二世在网上关注过几个历史博主,知道他们天天拿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们互相比较拉踩,俗称赛博斗蛐蛐。
万一自己因为这雕像留下了什么千古美名,结果翻史书一看,你的“青天”功绩其实就是微服私访时解决了一下当地的恶毒乡绅……
那他的名声可就别想要啦!
但民间倘有什么风声流传,光靠禁是禁不住的。后世的《大义觉迷录》就是前车之鉴。扶苏只好捏着鼻子。每天兢兢业业地司理起刑狱之事,好让自己后世不要嘲笑得太狠。
至于后来他因“青天”之名和划时代的法治思想,屡屡登上后代法制史教材。乃至于成为法律人士的祖师爷之一,就是另一桩故事了。
不止是后来当了皇帝,其实自扶苏他派兵围住了张家,众目睽睽之下把张复财绑住出了宅门,塞进衙门的监狱,“小青天”的外号就立刻流传开了。
这件事反传回扶苏的耳朵,他听完之后就沉默了:“原来怀仁县人苦张家久矣啊。”
明明对他全无了解,只听闻他抓了张复财就能好感顿生,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大家伙太恨张家了。
那他这个青天,还真得当下去。
扶苏拉上了苏轼,又点了几个识字的士兵,在衙门前摆了一排桌椅板凳。干什么?免费帮人写诉状状告张家!也接待被告人其他城中大户!
大家搞快点儿,有冤申冤,有仇报仇啊!
其实,扶苏早在衙门前设立了登闻鼓,但效果却一般般。不是谁都愿意众目睽睽下诉说自家的伤疤。而且怀仁县迄今没有靠谱的县官和师爷——之前的早被狄青进城时,当着县里人的面一刀砍了。
据说,当时也是一片叫好。
“那不对啊?”苏轼问道:“就算我俩去写诉状但还是没人审案子啊?”
扶苏:“有啊?”
“谁啊……难道殿下你指的是,我俩?”苏轼瞪大了眼睛,顿感压力山大:“不,不行的吧,我只会背《天圣令》和《宋刑统》,不会背《大辽律》啊!”
“不,也不对。当年沛公被老秦人喜迎入关不也只约法了三章?咱们也可以效仿高祖啊。”
无意中被插了一刀的扶苏:“……”
意思我都明白,但你举例子的时候能不能换个?扎得我心痛啊。
扶苏捂着心口,缓缓吐出一口气,惹得苏轼不明所以地看过来:“没办法,平息民愤、收拢民心是当务之急,但不能把张家人处死了之。这是在给后来的大宋官员治理上难度。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当一回‘青天’了。”
“而且这里,唯一系统熟读过律法的也只有你我,咱俩不上还有谁上?”
“还真是。”苏轼托着下巴沉思。多年的编辑经验让他职业病发作:“但这次机会难得,大家都关注着……”
“殿下,你说,我们趁机在怀仁县兴办《求知报》怎么样?前几期的素材就用审判张家的过程和经典案例,大家肯定都会买来看,等读者群固定下来,后面我们再慢慢改成别的内容。”
起号教程。
扶苏脑海中突然浮现这四个字。
“你以后……一定会成为大博主的。”
“博主?那是什么?”苏轼不明所以:“是大官的意思吗?那就借殿下吉言——”
回去就可以升官啦,嘿嘿!
就这样,兼具多重目的的“赵氏苏氏免费代谢诉状业务”在官衙大门前堂堂开业,不收取任何费用,一条龙服务,童叟无欺!
其声势之隆重,还把原本被冻风寒卧床养兵的段银儿引来了。她远远来到县衙的大门外,就看到两排士兵带着刀立于两侧,负责维持纪律。中间留出用于排队的空地,人山人海、人头攒动。
“姓名?”
“俺、俺叫许二妮儿。”
“年龄?”
“五十七……六十多啦!”
扶苏闻言,抬头看了一眼,赞了一句“您真高寿啊,外表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哄得来告状的人骄傲地露出了半颗门牙。
“所以,您要状告张家的谁?什么事儿?”
一说起这个,许奶奶拧着手指,踌躇不安了起来:“俺要告的状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还、还算数吗?”
现代刑法追溯时效最长是二十年。但还是这句话,这里是古代。
“您要告状的人活着,且承认,就算数。”
许婶子立刻精神一振:“俺要状告张家老二毁俺的名声清白!当年俺要嫁人的时候,去他家铺子里买东西,就被他说偷了他家东西,其实压根是他自己亏钱了,赖在俺女儿的头上!害得俺二十多年抬不起头!”
扶苏提笔刷刷刷在纸上埋头苦写。
其实许婶子正心中忐忑着,就这么鸡毛蒜皮一件小事,值不值得她专程跑到县里说道。丈夫、甚至儿子女子都劝她算了,可是许婶子就是咽不下这一口气!
许婶子端详着扶苏的样子,他没有像村里那些人一样跟着啐几口张家,然后叹着气劝她“咱们能怎么办呢,日子还不是照样过”。
其实她知道,有的人并不是十分信她的话,觉得张家是她女儿偷东西的背锅侠。
此刻的许婶子心中颇为空落,因为没得到惯常的附和回应,她不禁猜测:这小小的青天大老爷会不会不支持她?
但她转念一想,这可是笔和纸呢!好贵的!小青天大老爷正在为她用纸和笔写字,不比随口一句附和值钱多了?
如此想着,她又安心下来。
扶苏对许婶子的心理活动一无所知,他记录完时间、地点人物后,又问道:“如果这个案件真相大白了,您介不介意我们将它登载在报纸上?就是写在纸上,可以给你到处给人看!”
许婶子听懂后:“不介意!不介意的!俺要证明俺是清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