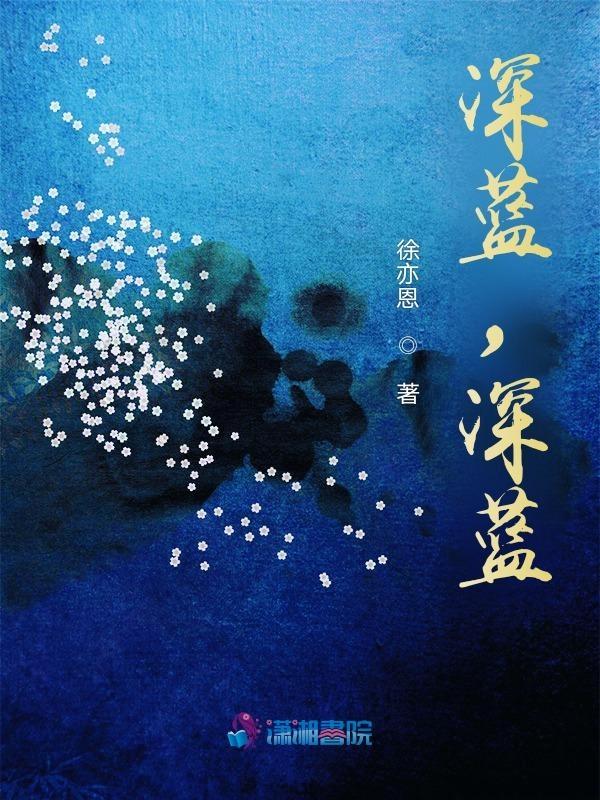富士小说>驯服恶役的日与夜最新章节更新内容 > Chapters 46(第2页)
Chapters 46(第2页)
“进去之後,你千万不要冲动,等着我们去找你。”虽然嘱咐了一路,但奥佩莎还是担心他莽撞的性子,重又叮嘱了一遍。
“好。”辛德瑞尔依旧是淡淡答应,这却并不能平复奥佩莎不安的心情。
时间紧迫,她也只能选择相信辛德瑞尔。
解开卢多维克身上的镣铐,她推了把卢多维克:“去吧。”
卢多维克双目无神地走在前面,带着他们走向奴隶场的大门。
守卫看到远远走来的卢多维克,立马弯腰行礼:“卢多维克先生,晚好。”
“嗯。”卢多维克机械地应着,说出了阿姆拉早已设定好的话,“我带着大人要的人回来了。”
守卫看了眼垂着头,脏兮兮的辛德瑞尔,又看向身後的奥佩莎和阿姆拉,有些疑惑:“我记得,大人是带着三个人出去的。”
“是的。”卢多维克继续说,“那位去喝酒了,毕竟任务艰难,我也理解他想放松的心情。”
“原来如此。”那守卫豁达地大笑两声,“卢多维克先生还真是善解人意,请进请进。”
通行的很顺利,连纹章都没有看。
看来卢多维克的地位在交易行里都是不容小觑的存在。可一个神职人员,甚至只是个不能自保的画师,又是为什麽会跟交易行的人有联系?
他侍奉的人到底是谁?
难道,是教会的人?
“一会记得屏住呼吸。”辛德瑞尔的声音忽然响起,很低,但足够两人听见。
“什麽?”
种种疑惑萦绕在心头,奥佩莎困惑着,走进了奴隶场。
刚一进门,一股刺鼻的恶臭便猛地钻入鼻腔——那气味仿佛盛夏时节堆积多日的垃圾腐烂发酵後,混杂着酸腐与霉味的浓汤,熏得奥佩莎喉头一阵发紧,胃里翻江倒海,几乎当场就要反胃作呕。
她连忙屏住呼吸,扫视着周围,想找出到底是什麽东西能发出这样难闻的味道。
然而周围的景象使她瞳仁骤缩——若说世间有地狱,那这里便就是具象。
她一直以为黑市里贩卖奴隶的摊位已经足够残忍,将奴隶关在狭窄腐朽的牢笼,烈日暴晒,或是暴雨冲刷,每个人都面瘦肌黄,衣不蔽体。
然而这里,那样的景象属于再正常不过的。
昏暗的烛灯照亮了奴隶场的各处:男人如同屠宰好的猪肉,被悬吊在天上,仅仅为了检测他是否足够强壮;貌美的女人会被扒光全身,关在玻璃制的牢笼里供人观赏;而稍次的女人和孩童,会呈大字型被束缚,任人鱼肉,任人挑选。
“说了屏息。”看到阿姆拉和奥佩莎面如土色,辛德瑞尔叹了口气,“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曾经生活的地方。”
他丝毫没受到影响,继续道:“难闻吗,我们已经习惯了。因为无法行动,吃喝排泄都在方寸之地,长久堆叠出来的味道自然不会好闻。”
他指向居中的小木台:“甚至有些奴隶是专门用来为买客排解的,他们更惨。”
奥佩莎看去,居中的小木台上跪着一排奴隶,那些奴隶一看就是老弱病残,属于不合格的奴隶。
然而这里并不是直接处死或贱卖,而是剥削走奴隶的最後一丝利益,放在公共的地方,供买客肆意凌辱或殴打。
买客肆无忌惮地折辱着他们,稍微有些姿色的女人会好过一些,而其他奴隶却没那麽幸运,痛叫着,翻滚着,身上留下一道道触目惊心的疤痕。
那些疤痕早已溃烂发白,黄色的脂肪层像蜡质般失去光泽,粘稠的组织液不断渗出。更令人头皮发麻的是,几条乳白色的蛆虫正疯狂地往里钻噬,肥硕的躯体在腐肉间扭曲蠕动。
再看那些奴隶,疯掉是大多数,扯着伤口上的蛆一根根放进嘴里,痴痴呆呆地笑。少数没疯的,也只剩下半口气。
比起这里的奴隶,外面的奴隶甚至不能说是幸运,简直可以说是生活在天堂。
管理人员领着那些买客一一观赏,仿佛那些不是人,而是可以随意拿捏的玩物。
被展出的奴隶们甚至不敢发出哀嚎,只能匍匐在买客脚下,诚恳亲吻买客的脚背,请求他们能够带走自己,好像那样就能从暗无天日的黑里窥得一丝天光的亮。
可被带走後的命运是谁也说不准的。
无人能想象这些开怀大笑丶毫无人性丶像是披着人皮桀桀行走的恶魔能够善待这些奴隶。
整个奴隶场都充斥着荒诞而令人窒息的残酷——铁链拖曳的钝响与濒死者的呜咽交织,镣铐在瘦骨嶙峋的躯体上勒出紫红痕迹,监工的皮鞭留下一道道猩红血渍。
人性的丑陋在这里暴露无遗,没人觉得自己会有明天。
奥佩莎不忍心再看,强忍着怒火抠紧了掌心。
她根本无法想象辛德瑞尔过去是怎麽过的,又是如何在绝望中坚定自己要活下去。
若是她,可能一天都无法生活。
“接下来,我们要分头行动了。”奥佩莎低声说,“找到那个畜生,要他生不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