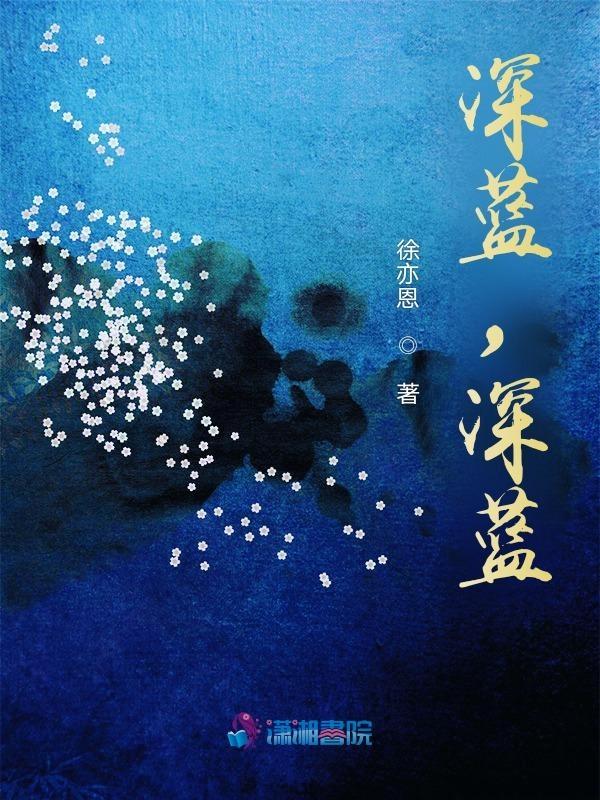富士小说>鱼玄机传晋江 > B 版结局BE不喜悲剧者勿入(第2页)
B 版结局BE不喜悲剧者勿入(第2页)
他们之间,不曾牵手,未及拥抱,没有任何肌肤的温热可以慰藉此刻的别离。然而,在这清冷的空气中,两个孤独而骄傲的灵魂,却在彼此的懂得和理解中,进行了一场最深切的拥抱与缠绕。完成一场无声的丶盛大的告别。
他转身,步履略显蹒跚地离开了房间,融入了门外的夜色之中。
玄机独自站在原地,良久,直到青杏小心翼翼地推门进来。
“娘子……”青杏担忧地轻唤。
玄机回过神,看向青杏,目光渐渐恢复了焦距和力量。
“青杏,”她轻声问,语气却异常坚定,“我欲离开长安,寻一处江南小镇隐居,前路或许清贫,你……可还愿跟着我?”
青杏毫不犹豫地跪下,声音清脆而坚定:“娘子在哪儿,青杏就在哪儿!青杏不怕清贫,只怕……只怕不能再伺候娘子!”
玄机俯身,亲自将青杏扶起,眼中终于泛起一丝真实的暖意。“好。那从此以後,我们主仆二人,相依为命。”
数日後,一辆简朴的马车驶离了温府。
车厢内,玄机倚窗而坐,看着窗外不断後退的景物。长安的轮廓最终消失在视野尽头,她轻轻合上眼。
她知道,她辜负了一份深沉的情意,选择了一条更为孤寂的道路。但她亦知道,唯有如此,她才能真正挣脱所有无形的枷锁,成为那个不为任何人附庸丶只属于自己的鱼幼薇。
长安一别,岁月不居。时光的洪流裹挟着个人的悲欢,奔涌向前。温庭筠与鱼玄机,这两个名字,在挣脱了彼此生命中最炽热也最沉重的交织後,如同星辰分轨,各自照亮了一片文学的夜空。
回到婺州旧宅的温庭筠,真正将身心沉入了江南的烟水与书卷之中。他不再刻意避世,亦不再强求忘情,而是将那份深沉的牵挂丶毕生的坎坷丶以及对世间情爱百态的通达洞察,尽数倾注于笔端。
他致力于词章的创作与整理,其词风秾丽绵密,精妙绝伦,尤擅捕捉闺阁情思丶离愁别绪的微妙瞬间,笔下女子形象活色生香,情致婉转。他编订《花间集》,其艺术趣味与创作实践,无疑为这部词集奠定了基石,被後世尊为“花间派”的开山鼻祖。
他的词,如“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写尽了富丽精工下的寂寞幽情;又如“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则将长夜无眠的相思之苦,刻画得淋漓尽致,成为千古传唱的名句。
他与李商隐并称“温李”,其诗才敏捷,八叉手而八韵成,典故富赡,色彩瑰丽。只是,晚年的诗作中,早年那份不羁与讥诮渐渐沉淀,多了几分阅尽沧桑後的苍凉与淡泊。偶有故人从长安来,谈及京中旧事,他大多默然倾听,只在酒酣耳热之际,或于无人见的深夜,会提笔写下一些无题的诗行,字里行间,依稀可见那个清丽倔强的影子,却已融入了更广阔的人生慨叹与历史烟云之中。
在无数个烛影摇红的夜晚,当他搁下笔,望向窗外南国寂静的星空时,心中所念,并非身前身後名,而是那个最终选择了独自远行的女子,是否也找到了她想要的安宁与自在。
鱼玄机,或者说,重新做回鱼幼薇的她,最终选择了太湖之滨的一处宁静小镇。她赁下一所临水的小院,开设了一间小小的女塾。她不再以“玄机”或“忘机”为号,只让附近愿读书习字的女孩们,称她一声“鱼先生”。
她的生活清贫而充实,白日里教导女童们识字读诗,讲述山川地理丶历史故事;夜晚则于灯下整理旧稿,撰写新的诗文。一个秋夜,她忽然想起许多年前,写给那人的诗,如今读来,别是一番滋味:
苦思搜诗灯下吟,不眠长夜怕寒衾。
满庭木叶愁风起,透幌纱窗惜月沈。
疏散未闲终遂愿,盛衰空见本来心。
幽栖莫定梧桐处,暮雀啾啾空绕林。
彼时是带着期盼与埋怨,如今则是彻底的释然与平静。她将旧稿轻轻合上,不再有波澜。
她的诗风,在经历了大起大落丶大喜大悲之後,褪去了早年的部分清冷与後来的激愤,呈现出一种洗尽铅华的澄澈与深邃。
笔下既有“吴蚕缠绵,犹作茧自缚”般对过往的释然,也有“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豁达。她写江南的杏花春雨,写太湖的烟波浩渺,笔触细腻而意境开阔,既保留了女性视角的独特敏感,又蕴含着不输男子的胸襟气度。
那本署名“杨澈”的《西行漫记》,在她隐居期间经过修订与增补,悄然在江南士人间流传,其价值愈发被有识之士所推崇,被誉为“舆地之奇书,忧世之良言”。
偶尔,她会从往来商旅的闲谈里,听闻那个远在婺州的名字,听闻他词名日盛,被誉为“一代文宗”。她总是静静听着,面上无波无澜,只在无人时,会临窗抚琴,弹一曲《幽兰操》。
他们终究,如她所愿,相忘于江湖,却又以另一种形式,永恒地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