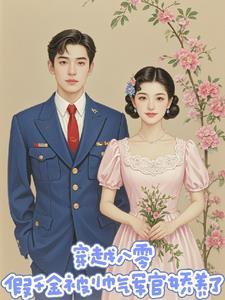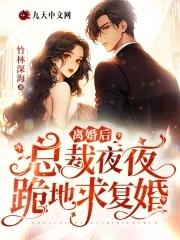富士小说>鱼玄机传奇色彩 > 风波再起(第1页)
风波再起(第1页)
风波再起
起初,是些慕名而来的文人雅士。他们或持帖拜访,或借故游观,只为能一睹这位传奇才女的风采,若能与“忘机道人”品茗论道丶求得片纸只字,更是足以在友朋间引以为傲。
静虚观主对此乐见其成,甚至特意将前院一间偏殿收拾出来,辟为茶室,备上清茶素点,供玄机与来访文士交谈。她则在一旁含笑周旋,言语间不着痕迹地提及观中清苦丶殿宇待修,引得不少人慷慨解囊,捐输香油。
玄机虽不喜应酬,但见来访者亦多是真心慕才而来,便也渐渐放下心防。她与文士们论诗,品画,乃至谈及西域风物丶朝堂时局,亦常有惊人之语。她那融合了个人际遇的深沉感慨与超脱视角的诗风,愈发为世所重。《西行漫记》虽署名“杨澈”,但其真实作者乃鱼玄机的消息也逐渐传开,更增添了她的传奇色彩。
一时间咸宜观“云栖院”渐渐成了长安城内一个特殊雅集。
静虚观主心中暗喜,更是倾力支持。她甚至挤出银钱,为玄机刊印诗集,题名《忘机集》,收录了她近年来的诗作精华。诗集一经问世,因玄机之名与其中真切的沧桑感慨,求购者甚衆,连宫中也有人寻来阅览。
这日午後,云栖院内正举办一场小规模的清谈。玄机与几位相熟的文士品茗论道,话题从近日诗文渐次延伸到儒释道三家义理,气氛融洽。
然席间一位约莫二十出头的士子,此刻却忽然放下茶盏,声音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清亮与不加掩饰的愤慨:
“……方才听诸位高谈阔论,皆赞忘机道人才情高妙,学生却有一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他目光转向主位的玄机,语气带着少年人特有的锐利与执拗,“女子纵有才情,亦当知礼法大防!圣人云,女子无才便是德!即便略通文墨,也当藏于深闺,修身养性,方合妇道!如今竟在这道观之中,公然召集男子,诗文唱和,抛头露面,成何体统?此等行径,岂非玷污佛门清修之地!”
一番话如同油入沸水,席间顿时一静。
静虚观主作为主人之一,立刻沉下脸色,正欲开口。玄机却微微擡手示意,她迎向那年轻士子咄咄逼人的目光,神色平静,
“才非女子之过,无才何以明心?世间既许男子以才博名,何独禁女子以文抒怀?我以诗明志,以文会友,非为越矩,实为守心——心之所向,才之所往,这便是我的‘德’。”
年轻士子面红耳赤,强自争辩:“可《女诫》有云——”
“《女诫》教女子柔顺,却未教女子蒙昧。”玄机轻轻打断,“班昭着《汉书》,蔡琰作《胡笳》,——这些青史留名的才女,莫非在小居士眼中,都成了无德之人?”
她将茶盏轻轻放下,目光扫过满座文士,最後落回那年轻人身上。
那年轻士子在玄机的诘问下,张口结舌,额角沁出细汗。
“这位小居士!”静虚观主也适时接话,“今日雅集,乃贫道与忘机道友共同主持,邀请的皆是慕道向学之雅士,在此切磋学问,啓迪智慧,正是我玄门修行本分,何来‘败坏’一说?小居士登门做客,妄逞口舌之利,污蔑主家,莫非便是圣人所教的‘礼’?”
席间另一位年长文士也拈须开口道:“贤侄此言过于偏颇了。忘机道人乃方外之士,才情见识令我辈亦深感佩服。清谈论道,何分男女?以才学相交,正是佳话。你年纪尚轻,不可妄加评判,失了礼数。”
那年轻士子被两人接连反驳其“年少”且“失礼”,顿时面红耳赤。他梗着脖子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几乎是逃也似地悻悻然拂袖而去。
一场风波,暂且平息。
雅集散去後,静虚观主来到玄机房中,语气带着些许无奈:“不想今日竟有如此莽撞的年轻後生混入席间,让道友受此无妄之扰。”
玄机神色平静,眼底却是一片清冷:“观主应对得当,玄机感激。只是,‘礼法’二字,重逾千斤,今日避得开当面诘难,他日避不开背後暗箭。”她感到一种深切的无力与惘然。
静虚观主默然片刻,叹道:“是啊,人言可畏,衆口铄金。但道友之才,如锥处囊中,其末立见。岂能因噎废食?我等行得正,坐得直,但求心安罢了。”
这日玄机信步到咸宜观的大殿,仿佛唯有在那慈悲垂目的神像前,方能寻得片刻的慰藉与答案。
玄机静静瞻仰正中那尊垂目含笑的观音玉像。佛像面容丰润,衣纹流转如云,手指轻拈杨柳枝,仿佛下一刻就要把甘露洒向人间。
正出神间,身旁传来一道温和的声音:“道人静观此像,神游物外,可是心有所悟?”
玄机回过神来,见是一位年约五十的妇人,身穿沉香色杭缎褙子,发间只簪一支素银如意簪,气度沉静雍容。身旁还跟着一位头发花白丶面容慈祥的老嬷嬷。
玄机合十行礼:“贫道忘机,见过二位居士。夫人眼明心亮。方才见菩萨垂目之相,确实想起灵山会上那段公案——世尊拈花,百万人天皆不解其意,唯有迦叶尊者破颜一笑。”
老妇人微微一笑,介绍自己,“老身姓郑,这是秦嬷嬷。”
然後眼中微动:“道人看得真切。世尊拈花是‘示现’,迦叶微笑是‘领悟’,这一示一悟,正是以心□□。”她擡袖指向观音玉像,“你看这尊菩萨,虽未拈花,却以全副法相示人。她垂目之处,便是拈花之时;衆生若有所会,又何尝不是迦叶一笑?”
玄机凝神思索,心头豁然清明:“夫人的意思是,这大殿便是灵山,此刻便是当年?”
“正是。”郑夫人微微点头,“月本常明,云散月现。道人既见月光透云,便是好消息。”
玄机闻言心头一震,轻声道:“多谢夫人指点。贫道号曰忘机,亦知当泯除机心,归于自然。然有时仍不免在文字中求道,却忘了‘道在平常’之理。”
郑夫人却摇头:“诗文虽是小道,也可映照性情。忘机之号甚好,能忘机,方能得真趣。道人笔下那些塞外风光,非胸有丘壑者不能写出。”
郑夫人继续道:“你西行漫记中记录慧明禅师讲法,慧明禅师亦曾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道人既已身在咸宜观,何不将此处当作道场,将往来文士视作同修?以诗为镜,以文为筏,渡人亦渡己。”
这番话如春风化雨,涤尽玄机心中最後一丝迷惘。
她起身,向郑夫人深深一揖:“多谢夫人指点迷津。玄机明白了。”
郑夫人含笑点头。
玄机又将人请到观中一处僻静厢房。两人从佛像艺术到诗文创作,从西北风物到人生际遇,郑夫人说到“当年我随外子赴任,在敦煌一住数年,沙州人物风貌,与中原大异,女子持家丶经商丶乃至参与社事者所在多有,才识胆魄,丝毫不让须眉。可见天地生人,赋予灵性,本无分男女。”
玄机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光亮:“夫人曾在敦煌居住?”
“正是,”郑夫人眼中泛起回忆之色,“算来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节,每日可见商队驼铃,响彻沙碛;石窟壁画,绚烂夺目。我等虽客居异乡,却觉心胸为之开阔。道人在《西行漫记》中描绘沙州风物,提及莫高窟壁画‘飞天衣带如云,仿佛真要破壁而去’,当真形容得妙!我当年初见,亦是这般震撼。”
玄机许久未遇如此投机的谈话,不知不觉间,初时的拘谨已悄然消散。她甚至说起早年与温庭筠修县志的往事,郑夫人听得专注,眼中时有会心之色。
日影渐斜,殿内光线转暗。郑夫人望着窗棂间透入的馀晖,轻声道:“与道人一席谈,如饮醇酒。可惜天色已晚,老身该告辞了。”
玄机心生不舍:“夫人若有闲暇,欢迎常来观中走走。”
郑夫人深深看她一眼,目光温和:“道人珍重。以才情笔墨安顿自心,便是最好的修行。世间纷扰,稍远一些,反倒能看清本心。”
二人相互施礼告别,身影缓缓消失在殿外长廊尽头。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 他死后众生皆悔:楚煊聿秦婉结局+番外楚煊聿秦婉
- 楚煊聿却违背家训,求丞相劝诫陛下下旨判楚煊聿此人,生不得踏足大梁,死不得认祖归宗!我怔在那里,几乎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