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小说>不会武功的我只好开马甲[综武侠 > 人自醉 宁醉 芜湖(第2页)
人自醉 宁醉 芜湖(第2页)
而将人“地咚”的宁醉低头看着令东来,眯着双眼整出一副“好困睁不开”的样子,慢悠悠地“啊”了一声应道:“不好意思,我好像喝醉了。”
衆所周知,绝大多数喝醉的人都会说自己没醉;而说自己已经醉了的人,要不是有理智丶有自知之明,要不就是在骗人的——宁醉无疑是後者。令东来当然不至于分辨不出一个人是真醉还是假醉,但他此时只是看着。
人影挡去几分烛火与月色,残存的朦胧微光映得令东来的脸似乎罕有地多出一抹慵懒,黑白分明的双眼一刻不离笑着俯身看他的宁醉,两人便是如此凝视片刻,然後——攀上宁醉肩膀的右手以及在其腰侧是左手一同发力,以近似擒拿缠斗的手段瞬间将二人的位置调转过来!
其实在令东来有所动作的那一瞬间,宁醉便条件反射地同时出手做出应对。还不到半个呼吸的时间,两人已经闪电般近距离过招拆招好些个回合,可惜宁宗主最终还是成了被摁倒在地的那个——双手还都被压过头顶。
宁醉为此懊恼半秒,而後便擡眸扬眉,玩味地抢先问道:“怎麽,担心我酒後乱性,对你图谋不轨,所以先下手为强?”
令东来却是反问道:“这就是你有心灌醉我的真正目的?”
对此一问,宁醉当场叹了口气,爽快地承认了:“可惜啊,你的酒量瞧着不比我差多少,不知道何时才能醉过去——所以我只能直接下手了。”
“若然你欲与我同床,本就无需如此作为。”令东来隐隐流露出一丝疑惑和不解,“你若直言,我不会拒绝。”
宁醉则是又叹了口气,他明明同样没有恋爱经验,偏偏说得头头是道:“你不懂,这叫情趣——这种事情若总是直来直往,那就没有半点意思,很快就会腻了。”
看着令东来若有所思的神色,宁醉暗中尝试让自己的手脚脱离桎梏,然而并未成功。令某人不止劲大,而且还挺有巧思——想要不引起其注意便脱身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如果用力挣脱,则是会被自然而然地放开。反正宁宗主不急着改变姿势,于是他很快就放弃挣扎。
不过令东来在下一刻却是主动松开手,并且站起身将另一坛尚未喝光的酒提在手上。宁醉也懒得转移位置,只是一个仰卧起坐,便曲着腿在地上坐着,擡头问道:“你这是要干嘛?”
“继续你欲行之事。”令东来顿了顿,“不过我亦不知自己酒醉以後会如何。”
“其实也没必要彻底醉过去,没有意识反而不美——你有这份心就够了。”闻言,宁醉稍微愣了愣,随即双眼一亮,跳起来夺过酒坛子将其重新放回到桌上,继而将人推到床上,“我们可以直接进行下一步!”
最後一个字音含糊地融化在交叠的唇齿之间,而这一回,宁醉并未收敛,生涩又坚决地加深这个吻。令东来从来不会在这种时候闭上双眼,宁醉亦如此,两个空有理论知识的武者以研究的态度先後在对方身上进行不同的实践。
蜡烛“哔啵”的响声正好掩盖过唇与唇之间分离时的轻微水声,宁醉下意识地探出舌尖舔舐过自己那相比之前更红艳的上唇,右手则是有意无意地放在令东来的腰带上:“你应该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麽,真的不介意丶不後悔?”
令东来凝视着眼前人,视线从其张扬的面容聚焦到艳红的双唇,又轻飘飘地垂落到颈上那一枚在衣领间若隐若现的小痣。
其实他一直都在看着宁醉,每时每刻都在观察。然而于此时此刻,是昏黄的烛火引来了暧昧的氛围也好,是“仙人醉”的後劲终于到来也罢,这位无上宗师的目光不再如同往日那般缥缈莫测,它第一次沉淀出几分属于人间红尘的颜色。
令东来蓦然问道:“同样的问题,我亦需要你的回答——你当真不介意丶不後悔?”
“嗯?”宁醉尚未回答,顿时察觉令东来正在故技重施。尽管他吸取了之前的教训,与对方多过了几招,但仍是再一次被调换了位置,现在躺床上的又成了他。
好在这次他总算没有被彻底控制住双手,在被令东来压倒在床褥上时,他眼疾手快地抽走对方的发簪——墨色的长发如瀑散落,垂到宁醉的脸上和身上。宁宗主刻意用另一只手挑起那一缕掺杂在黑色之中的白发,将其拈至唇边轻轻一吻:“你似乎挺执着于上位,嗯?”
不等令东来回应,宁醉又紧接着道:“算了,反正我无所谓——我很确定我当下不会介意,也不会後悔。那麽你呢?而且……你知道接下来要怎麽做吗?”
令东来没有取回自己的发簪和头发,甚至主动动手解开了宁醉的发带,平日清冷高绝的他,在摇曳的烛光和昏暗的床笫之间,因披散的长发与不再整齐的衣着,莫名显得似乎有种艳鬼之姿。
不晓得令东来有没有在宁醉眼中看见如今的自己,又有怎样的想法,只听他以稍显低哑的声音回道:“我知道,且不会後悔。”
“嗯哼——”宁醉浅笑一声,便擡手打落床帘,“那就来试试吧。”
在轻薄的帷幔完全闭合之前,只见他的双手环在身上人的颈後,再次送上主动的一吻——而後,一夜旖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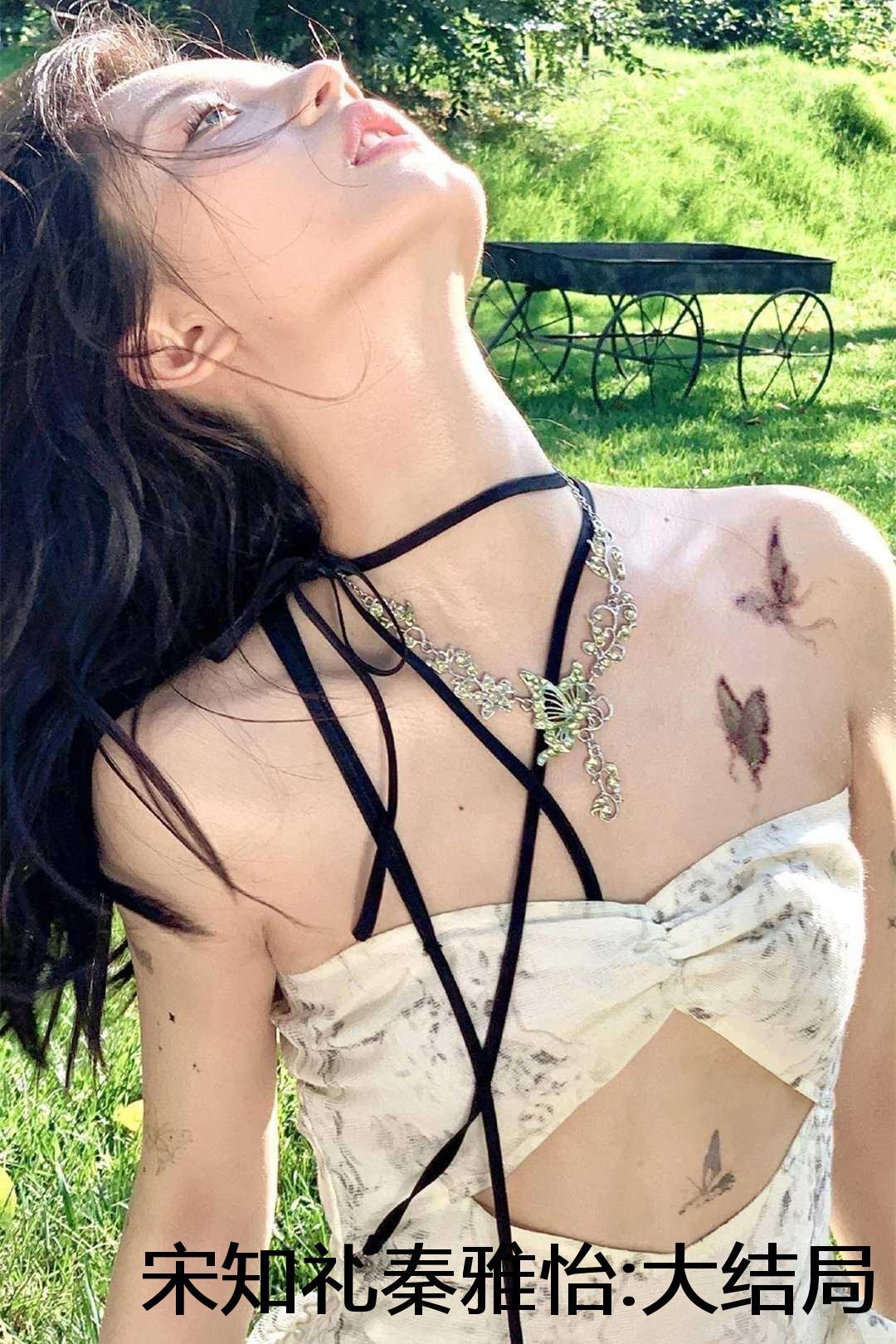
![盗版万人迷[快穿]](/img/478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