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小说>一千只猫的故事 > 第137章 多出来的房间(第2页)
第137章 多出来的房间(第2页)
烛光映照下,房间里的一切都拖曳着长长的、摇曳的影子,像一个个窥视的鬼魂。
这是一间不知道什么年代的婚房,一种喜庆和死寂交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
还没等我完全反应过来,后背上突然传来一股突如其来的拉扯力,那力道又猛又急,将我硬生生从衣柜背后的诡异房间里拖拽出来。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我毫无反抗之力,下一秒便重重摔在自己卧室的地板上,尾椎骨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
我撑着地板勉强坐起身,心有余悸地抬头望向衣柜——那块背板还半敞着,缝隙里隐约能瞥见方才房间的残影。
我再也不敢踏近衣柜半步,只能小心翼翼地挪动身体,一点一点站起身,与那个藏着秘密的衣柜保持着足够远的安全距离。
缓了好一会儿,我才又瘫坐在卧室的地板上,后背紧紧贴着冰冷的墙壁,望着衣柜深处那个不断变幻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洞口。
它像一场有规律的噩梦,周而复始。
我开始记录衣柜门板后房间的变化:周一,维多利亚书房;周二,医院停尸间;周三,诡异婚房……规律似乎存在,但毫无逻辑可言。
我试过在场景刚要变化时猛地冲进去,可每次都会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狠狠推开。
我也试过用厚重的书本、结实的木棍卡住衣柜背板的缝隙,可每次场景变化后,那些卡门的东西不是凭空消失,就是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卧室的某个角落。
走投无路时,我甚至报了警。
两名警察赶来后,里里外外仔细检查了衣柜,用手敲打着每一寸背板,可最终只得出“衣柜结构完好,没有异常”的结论。
他们看我的眼神带着明显的怀疑,像是在打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最后才委婉地建议我“多休息”。
我快要被这个凭空多出来的房间逼疯了,我都不敢在卧室睡觉,只能蜷缩在客厅的沙上。
生活的拮据让我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另寻住处,只能暂时被困在这个充满诡异的出租屋里,日夜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下一次变化的来临。
周四这天,我依旧蜷缩在客厅的沙上,眼睛因为连续多日缺乏睡眠而干涩痛,却还是死死盯着卧室衣柜的方向。
时间差不多了,衣柜深处的黑暗再次开始蠕动,像一滩浓稠的墨汁被无形的手搅动,景象逐渐清晰。
这一次,既不是华丽的维多利亚书房,也不是阴森的停尸间或诡异的婚房,而是一间看起来极其普通的老旧起居室。
房间里光线昏暗,只有角落立着落地灯散着微弱的昏黄光晕。
其余的家具——沙、茶几、梳妆台,全都蒙着一层厚厚的白色防尘布,在昏暗的光线下,像一个个沉默矗立的幽灵。
空气中漂浮着无数细微的尘埃,它们在落地灯的光柱里缓缓飘浮、旋转。
比起前几日那些风格强烈、充满冲击感的场景,这里显得太过平常,可正是这份“平常”,却更添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和死寂。
就在我稍微放松警惕,想着“这次或许没那么可怕”的刹那,我的呼吸突然停滞了——
因为我看到,在房间的中央,背对着我,坐着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件墨绿色的旗袍,布料上绣着暗色的刺绣花纹。
头在脑后挽成一个光滑的髻,髻上没有任何装饰,只露出一段白皙修长的脖颈,却透着一丝不自然的僵硬。
她坐在一张梳妆台前——那梳妆台刚才明明还被白布盖着,现在却显露出来——正对着一面椭圆形的镜子,手里握着一把木梳,一下一下,极其缓慢地梳着头。
“沙沙——沙沙——”
木梳划过丝的声音很轻,却像带着某种穿透力,清晰地传到我的耳朵里。
活的。
这个房间里,第一次出现了活物!
我僵在原地,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手脚冰凉,连呼吸都本能地屏住了。
我想移开视线,想逃跑,但身体像被钉在了原地,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旗袍女人的背影。
然后,一丝极轻极轻的哼唱声,飘了出来。
那调子很古怪,忽高忽低,不成章节,更像是某种不成曲调的呢喃,又像是一被遗忘了许久的古老童谣。
歌词模糊不清,但那旋律……那旋律像一根冰冷的针,猝不及防地刺入我的记忆深处。
我想起来了。
很多年前,在外婆的葬礼上,守灵的那个夜晚,我迷迷糊糊睡在偏房的草席上,半梦半醒间,似乎听到过类似的、缥缈的哼唱声。
当时大人说是我做梦,或者是风吹过灵堂挽联的声音。
那感觉并不愉快,带着一种葬礼特有的悲伤和诡异,被我深深埋藏。
可现在,这个女人,在这个诡异的房间里,哼着这只可能存在于我童年模糊记忆和梦境里的曲子!
就在这时,梳头的声音突然停了,那若有若无的哼唱声,也跟着停了。
整个房间瞬间陷入一片死寂,连尘埃落在地板上的声音都仿佛能听得一清二楚。
我看到,镜子里的那个女人,缓缓地、缓缓地抬起了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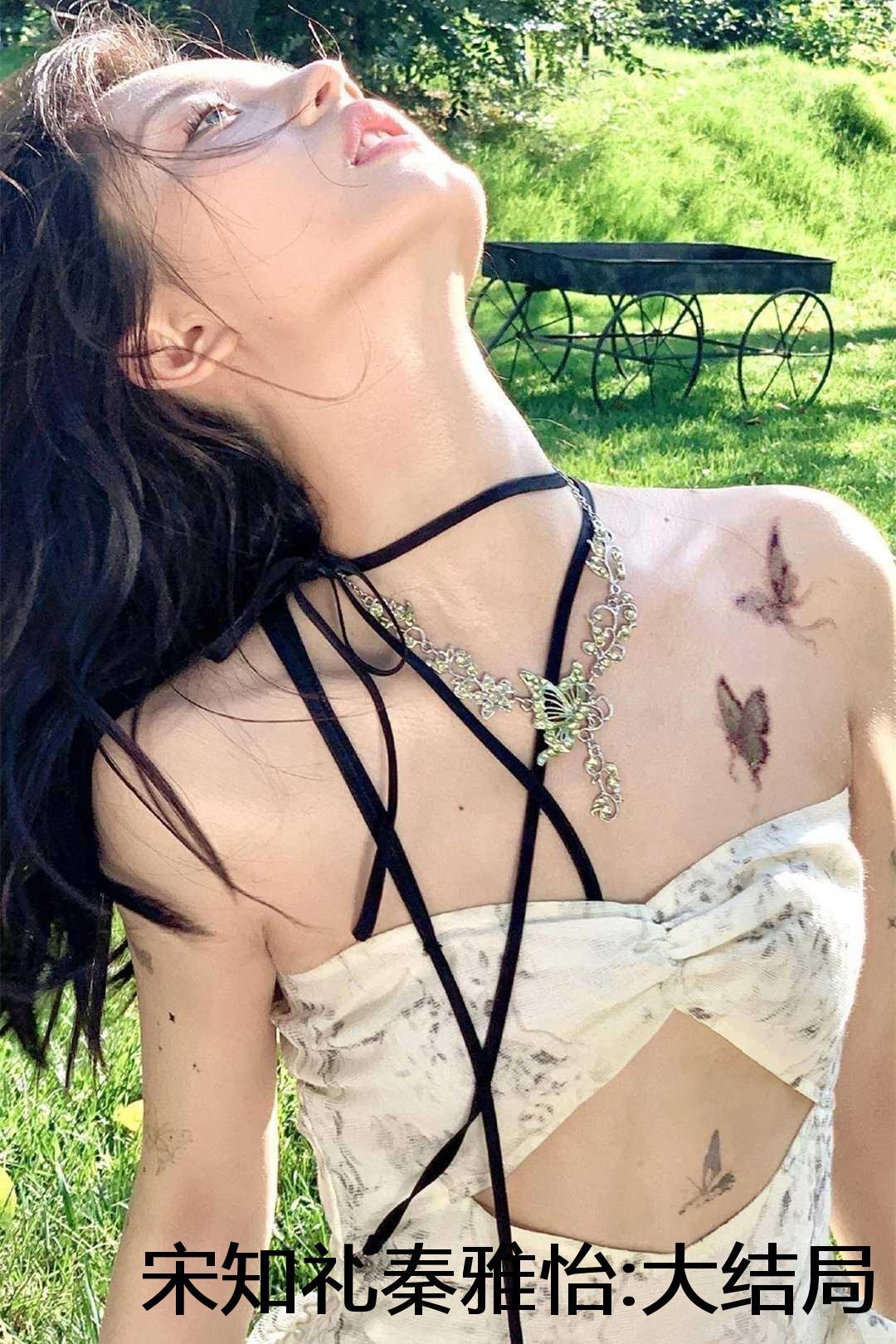
![盗版万人迷[快穿]](/img/478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