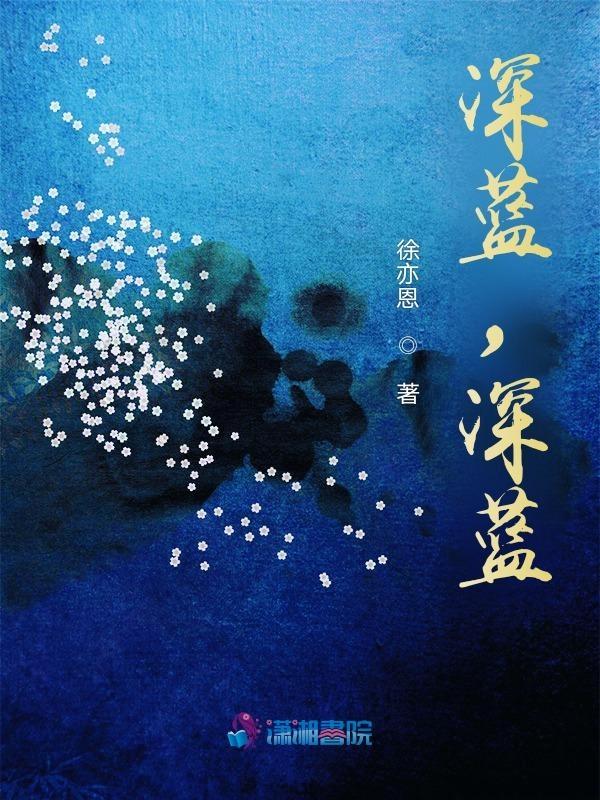富士小说>清川日常 > 第 27 章(第1页)
第 27 章(第1页)
第27章
孟寰海回衙那日,清川县像过了年。
鞭炮屑子铺了满街,百姓挤在县衙门口,抻着脖子看他们这位“青天大老爷”。孟寰海没坐轿,还是走着回来的。那身官袍洗得发白,穿在他清瘦的身上,空荡荡的,可脊梁骨挺得比衙门口的石狮子还直。
他没啥笑脸,也没说啥豪言壮语,只站在台阶上,扫了一眼底下黑压压的人头,说了句:“都散了吧,该干啥干啥。”声音不高,带着刚从牢里出来的沙哑,却像有千斤重,压住了所有的喧闹。
人群慢慢散了,带着心满意足,也带着新的盼头。
王主簿领着三班衙役,跪在二堂前,脑门子磕得咚咚响,鼻涕眼泪糊了一脸,说着“恭迎大人回衙”丶“小的们日夜悬心”之类的车轱辘话。
孟寰海没叫起,由着他们跪着。他背着手,在二堂里踱了一圈。桌子椅子还是老样子,只是积了层薄灰。他走到墙角,掀开那块旧布,那副石子棋盘安然无恙。他伸手摸了摸冰凉的棋子,没说话。
过了足有一炷香的功夫,他才转过身,看着地上跪着的一片後脑勺。
“都起来吧。”他声音平淡,“该干什麽,还干什麽。王主簿,把近一个月的公文卷宗,给本官搬来。”
王主簿如蒙大赦,连滚爬爬地去了。
孟寰海坐到那张熟悉的丶吱呀作响的太师椅上,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他知道,这些胥吏里头,有见风使舵的,有阳奉阴违的,说不定还有别人安插的眼线。但他现在没工夫清理,清川县等不起。
他得先稳住局面,让这架停摆了的县衙机器,重新转起来。
公文堆得像小山。大多是些日常琐事,但也有些棘手的问题积压了下来——赋税丶诉讼丶河道巡查……千头万绪。
他正看着,赵铁柱回来了。这汉子瘦了一圈,眼圈乌黑,但精神头十足,一进来就跪下:“大人!小的回来了!”
孟寰海看着他,脸上总算有了点笑模样,亲自起身把他扶起来:“好!赵铁柱,这次,你立了大功!”
“是大人洪福齐天!”赵铁柱憨厚地咧嘴。
“屁的洪福齐天!”孟寰海笑骂一句,“是你小子命大,腿脚快!”他拍了拍赵铁柱的肩膀,“从今天起,你就是县衙的捕头!”
赵铁柱愣住了,随即激动得脸通红,又要下跪,被孟寰海拦住:“行了,别来这套。去,把衙门里还能用的弟兄们都拢一拢,该巡街巡街,该站班站班,拿出点精气神来!”
“是!”赵铁柱声音洪亮,转身雄赳赳地去了。
安排了赵铁柱,孟寰海的目光落在那些关于赋税和春荒的公文上,眉头又锁了起来。周通判倒了,可百姓肚子里的饥饿,不会因此减少分毫。
他想起了番薯。
“王主簿!”他朝外面喊。
王主簿小跑着进来。
“去,打听一下,崔家庄子上那些番薯,长得怎麽样了?什麽时候能收?”
王主簿一愣,没想到大人回衙第一件关心的事,竟是这个。“是,下官这就去打听。”
王主簿退下後,孟寰海站起身,走到後院。那片曾经种过番薯的菜地,如今空着,杂草冒了头。他蹲下身,抓了一把土,在手里拈了拈。
希望,还能从这土里重新长出来吗?
与此同时,崔家别院。
崔敬祜也得知了孟寰海回衙的消息,以及他第一时间关心番薯长势的举动。
“看来,他是真把宝押在这‘土疙瘩’上了。”崔敬祜对管家道。
“庄子上回报,藤蔓长势极好,覆盖了整片坡地,若无意外,再过一两个月,便可开挖,看收成如何。”
“嗯。”崔敬祜点了点头,“收获之时,给县衙递个帖子,请孟大人前来‘共赏’。”
“是。”
管家退下後,崔敬祜走到书案前,看着上面一幅刚刚绘就的清川县水利草图。扳倒周通判,只是扫清了外部的障碍。清川县内部的治理,尤其是水利和赋税这两大难题,才是真正的考验。他知道,孟寰海必然要在这两方面动刀。
而这,也必然触及到包括崔家在内的,所有拥有大量田産的乡绅利益。
新一轮的博弈,已经在无声无息中开始了。
崔敬祜提起笔,在草图上某个关键河道节点,轻轻画了一个圈。
县衙里,孟寰海看着户房送上来的田亩册子,手指在“崔氏”名下那连绵的数字上重重敲了敲。
“清丈田亩,均平赋税……”他低声自语,眼神锐利,“这第二刀,该怎麽下呢?”
夕阳的馀晖透过窗棂,照在二堂的地面上,拉长了他沉思的身影。
清川县的新篇章,就在这沉静而暗藏机锋的氛围中,悄然掀开。青天回了衙,带来了光亮,也照出了前路上更复杂的沟壑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