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小说>霜天晓月梅译文 > 第 65 章(第2页)
第 65 章(第2页)
他笑笑,“你觉得那是错,那什麽才是对的?”笑意敛去,目光阴鸷,“你不是我,没理由替我原谅任何人,要麽不做,要麽做绝,这个天下将来一定是我的,只要我赢了,那一切都是对的。”
隽清起身,走到他面前,“你为了一己私利,引致北地动荡,百姓流离,你漠视一切,又怎会爱自己的子民,你做不了主君,才是万民之福。”
他盯着她,目光中慢慢多了一丝戾气,怒极反笑,又仿佛情绪抽离,盯着她问:“如果没有裴翊,你会不会喜欢我?”
“苍遥只是个幻影,画皮之下是个心狠手辣的魔鬼,有什麽资格谈喜欢?”
他沉默良久,突然起身一把拽住她的手腕,将她扯到自己怀里,伸开双臂箍住她,炙吻落在樱唇,危险的气息弥散,她惊诧地睁大了眼睛,他急促的呼吸间仿佛一种凶兽般可怕的残暴即将破牢而出。
她擡膝踢向他的腿,使全身的力气挣脱,吼道:“你疯了!”
他後退半步,稳住身形,修长的手指摸了摸唇,仿佛在回味刚刚那如兰的香息,“高隽清,这天下是我的,你也是我的。”
此刻的他是如此的危险,她辨出他寒眸中漫染的某种情绪,不禁心颤,见他又慢慢逼近,她本打算看准机会从他身侧冲出去,他看出她的心思,展臂抱住她,朝旁边床榻走去。
“放开我,阿斯蒙——”
他完全无视她的挣扎,将她抛到榻上,高大的身躯像一座山一般欺身而上压着她,招致她激烈的反抗,即使她会些武艺,现在的情况下,也不能撼动他半分,他顺势擒住她两个手腕钳制在头顶。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眸光愈加暗沉,附在她耳畔说:“靺鞨女子是不吝对喜欢的男子献出身体的,虽然你并不喜欢我,但我不在乎。”灼热的气息喷在耳间,惹得她一阵颤栗,他侧首吻她的脸颊丶耳垂丶脖颈。
“我恨你。”她倔强地咬着唇将头偏向一侧,他温热的指节箍住她的下颌,迫使她望着他的眼睛,“你不是说过吗,如果爱不能长久,或许恨可以。你早就恨我了,不介意再多一点,跟我一起下地狱吧,跟飞升成仙也没什麽区别。”说罢倏然吻上她的唇,贪婪地掠夺索取。
她能清楚地听见裂帛之声,他放开她的手腕,将她身上那套宫装撕裂。
温热的手掌抚过她的雪肤,沉沦在无底深渊中,绝望漫延到四肢百骸。听得他喘着气说道:“裴翊应该还没碰过你吧,那你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了。”
这样的情形她早有心理准备,但是身临其时,脑海中只馀下无尽的屈辱和悲愤,只能祈求自己豁出一切的豪赌能够渡过此劫。
她好似没了力气,不再挣扎推拒,甚至伸手揽住他,任他行事。
正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推开,寒风吹进,一个惊慌失措的手下闯进来,低着头不敢往里看。
阿斯蒙擡头吼道:“你想死啊!”
那手下哆哆嗦嗦地说:“君……君上,有急事。”
他阴鸷的眼神盯了那人片刻,可怕的沉默过後,他直起身,下榻理理衣袍,手下附耳小声说了什麽,他皱了皱眉,没有再回头,径自走出了屋子,屋门再次关闭,仿佛隔绝了两个世界。
隽清撑起身子,拢拢衣裙,从锦被下拿出刚刚趁乱藏
的东西——从他蹀躞带上摸下的匕首,匕首泛着寒光,也映出她脸上的清寒与决绝。
没几个时辰天便亮了,她观察了几日,这个时候是留守的人最少的时候。
她不得已换上阿斯蒙准备的那套绯色衣裙,轻轻打开门,门口守着的两个人本昏昏欲睡,立时一激灵,虎视眈眈地看着她。
她手捂着腹部,“二位,有没有热水。”
他二人对视了一下,却是不怀好意地笑,就在他们分神这一瞬间,她扬起手,匕首厉然劈划而过,鲜血溅洒,二人皆倒地。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外面零散的几个人看情形大骇,纷纷抄起兵器向她冲来,血溅到她脸上丶身上,裙上绽开深殷色的花,妖艳鬼魅。
她夺了一匹马,跃上马背,冲将出去,留下满院狼藉。
不知跑了多远,她失去了方向,只知还在山中,周围除了溪流草木,没有其它的东西。
她真的累极了,连日没有休息好,没有好好吃过什麽东西,一阵眩晕袭来,她摇摇晃晃从马上摔下。
古老的萨满信奉神明,不知如果这山中真有神明,是否会听到她的心愿。
强撑着起身,喝了几口山泉水,马儿已不知去向,她挨着一棵大树坐下,树木之粗壮甚至可以将她纤瘦的身体遮挡得严严实实。
这边山林中,一队人轻身缓缓靠近小院,伏掩于树木之中。
那个少年把玉镯拿到城中典当,被乔装的青云卫认出,那玉镯是国公府之物。
审问过後,大义信丶符昶带人,顺着线索追踪而来。
确认了位置,几面包抄,大义信一声令下,院门被攻开,本就乱作一团的逆党几已没有战力,反抗的就地格杀,留下一些请降的活口。
院中屋宇不多,大义信一间一间寻找隽清的踪迹。找到西边的一个屋中时,部下推开房门,屋内依然空无一人,他们刚想转身,大义信馀光瞥见了什麽熟悉之物,回头望向榻上,走近细看,分明就是隽清被掳走时穿在身上的那套内司官服,上面有早已干涸的点点血迹,更令他脑中“嗡”一声的是,那衣服前襟和下裳处被撕裂的破败模样。
活着的逆党被集中捆缚跪于一旁,青云卫严密看管着。
只见大义信周身冰寒地走过来,站在一个看似领头的逆党面前,“你们抓的那姑娘在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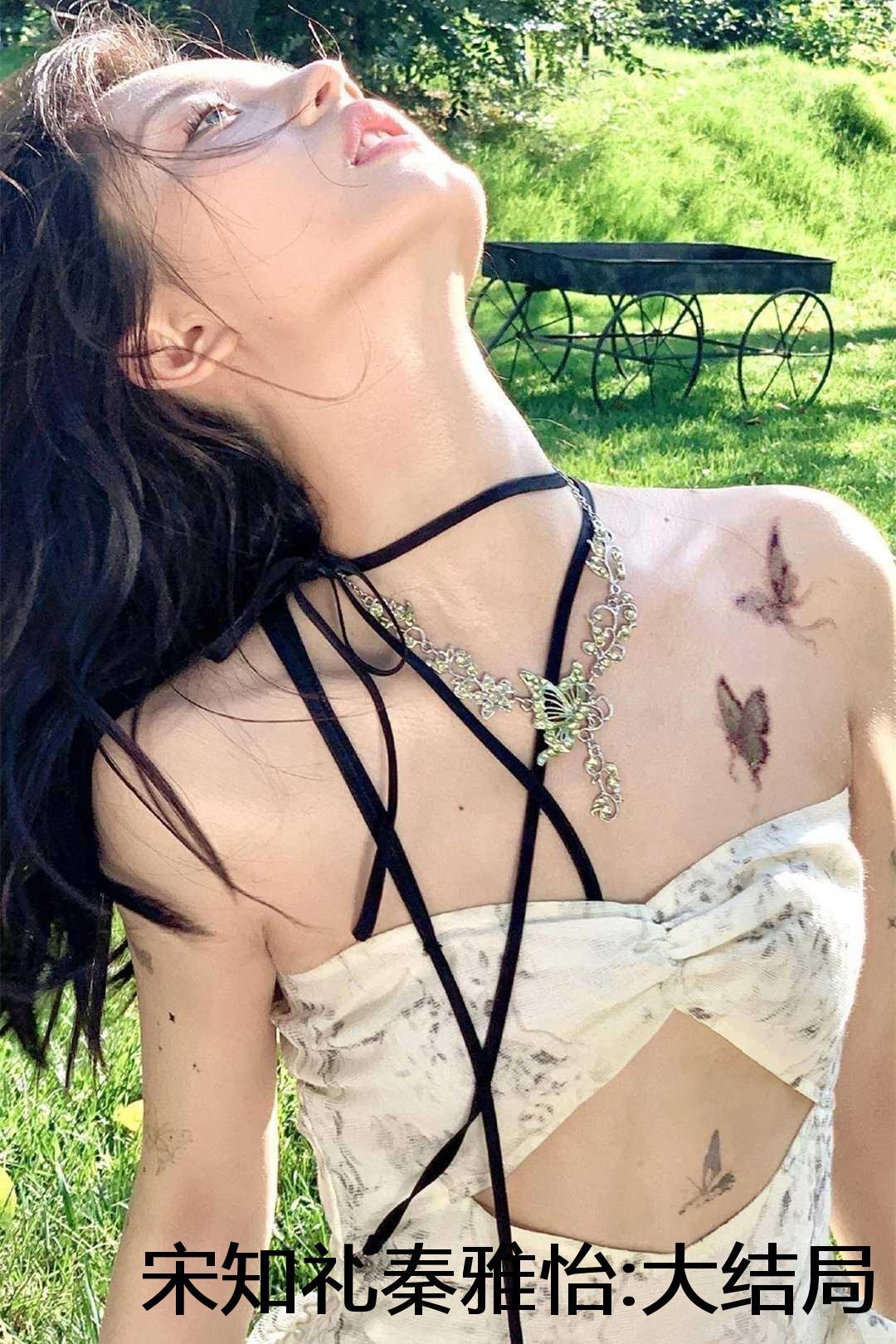
![盗版万人迷[快穿]](/img/478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