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小说>某年某月晴 某年某月阴是什么歌 > 第15章 P许愿(第2页)
第15章 P许愿(第2页)
“角度和光线肯定不一样,但毕加索坐在我怀里,我肯定能成为当代梵高。”楚北翎笑着接下,露出两颗白净的小虎牙。
林听岛也不是吃素的:“毕加索会不会坐在你怀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邢禹同学肯定不会坐在你怀里画。”目光扫向一旁的邢禹:“是吧,邢禹同学。”
邢禹一个走神没控制好手上力道,将削长脆弱的2B铅笔折断在画面上,他“啧”了一声,重新换了一支笔。
男生们笑得大胆张扬,女生们笑得腼腆,好几个朝两人看过去。
邢禹坐在楚北翎怀里画,这画面实在太美,她们不敢想,却有些期待。
午後炙热的光线将楚小少爷白皙的脸照得通红。
都怪邢禹,要不是他撕掉那张画,他也不至于吵完架,还惦记想要画邢禹,搞得他有多在意他似的。
林听岛笑意在脸上融化开:“怎麽的,有意见呀,要是不服气,等上人体造型,我安排你坐邢禹怀里,坐在教室中间给大家当参考,行不行呀!”
厉冬看热闹不嫌事大:“林老师我没意见,你赶紧安排,请你不要放过他们。”
有人出头带领,班里其他人也看热闹不嫌事大,纷纷起哄,我没意见的声音,在教室此起彼伏。
还有些胆子更肥,直接提出,扒。光两人看肌肉走向,画起来更有记忆。
林听岛拍了拍画板:“起什麽哄呢?还不开始画,谁吵,人体造型课谁坐教室中间给其他同学做参考,四个小时不准动。”
林听岛精准拿捏,班里一下子禁声。
对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们来说,正是爱动坐不住的年纪,坐在教室中间同给班同学做参考本就尴尬,还四个小时不准动,简直是当代酷刑。
林听岛和游魂一样在班级同学身後来回盯着,遇上她比较满意的夸一句,人就走掉了。
十三班有十几个和许图南一样,因为艺考轻松选择的美术班,只为考试而画,基础一般被她格外关注,特别是许图南,简直可以称得上灾难了。
许图南:“林老师,您别老站在我背後啊~怪凉的。”
林听岛扫了一眼许图南身上的铭牌,指着画面上的苹果,微笑着说:“许图南同学,请问,这个苹果拿出来给你吃,你吃不吃呀。”
班里一阵哄笑,许图南被这笑看得心里直咯噔,蚊子一样的嘀咕了几句。
林听岛:“你说什麽,听不见,大点声的呀~”
许图南汗流浃背:“这,这没办法吃。”
“是呀,没办法吃,那要重画的呀!”林听岛笑意更深,语调也更温柔,伸手点了点上头的苹果。
全班一阵闷笑,他们不敢笑太大声,怕被盯上直接开刷,只能憋出此起彼伏地鹅叫声。
许图南连忙上手用橡皮去擦苹果,林听岛阻止他,又拍拍手,打断班里其他在画画的同学:“不管是画石膏还是静物,已经开始上调子,能别大面积使用橡皮就别用,更别偷懒用笔擦着画面去磨出暗面,不然你们的画面看着会很脏,艺考影响分数,有这个习惯的同学,现在开始改掉。”
“你起来。”林听岛拍了怕许图南,又叫了班里几个基础较为薄弱的同学,让他们到身後,直接做范画讲解。
素描课结束後,他们又开始上色彩,也是直接画。
直到黄昏过渡到夜晚,天色从橙红慢慢晕染成忧郁的深蓝,他们才结束。
“所有人画纸干的可以现在交上来,没干的先摆在教室地上,等干了课代表来收。”
林听岛看向楚北翎:“楚北翎美术课代表,晚自习上课之前你来收,我的办公室在四楼,靠窗的那张桌子是我的。”
楚北翎应下。
林听岛离开美教,陆陆续续将被颜料弄脏的水桶和调色盘拿出去清洗,又重新回来收拾绘画工具。
楚北翎将五彩斑斓的白T从身上脱下,露出洁白的校服,他盖上颜料盒,拎上水桶和调色盘打算去清洗。
路过邢禹身边时,他忍不住看他一眼。
美术生上完课就和刚从垃圾场里掏垃圾出来差不多,身上手上没有一片狼藉的那都算不认真画画。
周围同学包括楚北翎,谁不是大花猫。
而邢禹却一点颜色都没沾上,除了尺骨这一侧的皮肤沾了些铅笔灰,整个人干净又清爽。
特别反人类。
干净又清爽的邢禹同学,正拿着刮刀,将刚刚被弄乱混合的颜料铲出来,又用湿巾将颜料盒边缘染色的白色塑料擦干净,最後用喷壶喷上一层薄薄的水才收手。
楚北翎实在佩服他,十年如一日的能保持,每次画完还有耐心清理颜料盒。
他能有耐心呵护颜色,也就只有在拿到新颜料的头两天,其馀时间搅合搅合完事。
邢禹盖上颜料盒,擡眸看过来:“有事?”
楚北翎低头扫了眼干净如新的颜料盒:“要是让软刀用你的颜料盒做范画用几次,你就老实了。”
林听岛第一堂课,软绵绵的语调说着最狠的话,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课後喜提这个称呼。
“哦,我还以为你想说,让我坐你怀里的事。”邢禹冷不丁的冒了这样一句。
楚北翎楞了半秒:“你有病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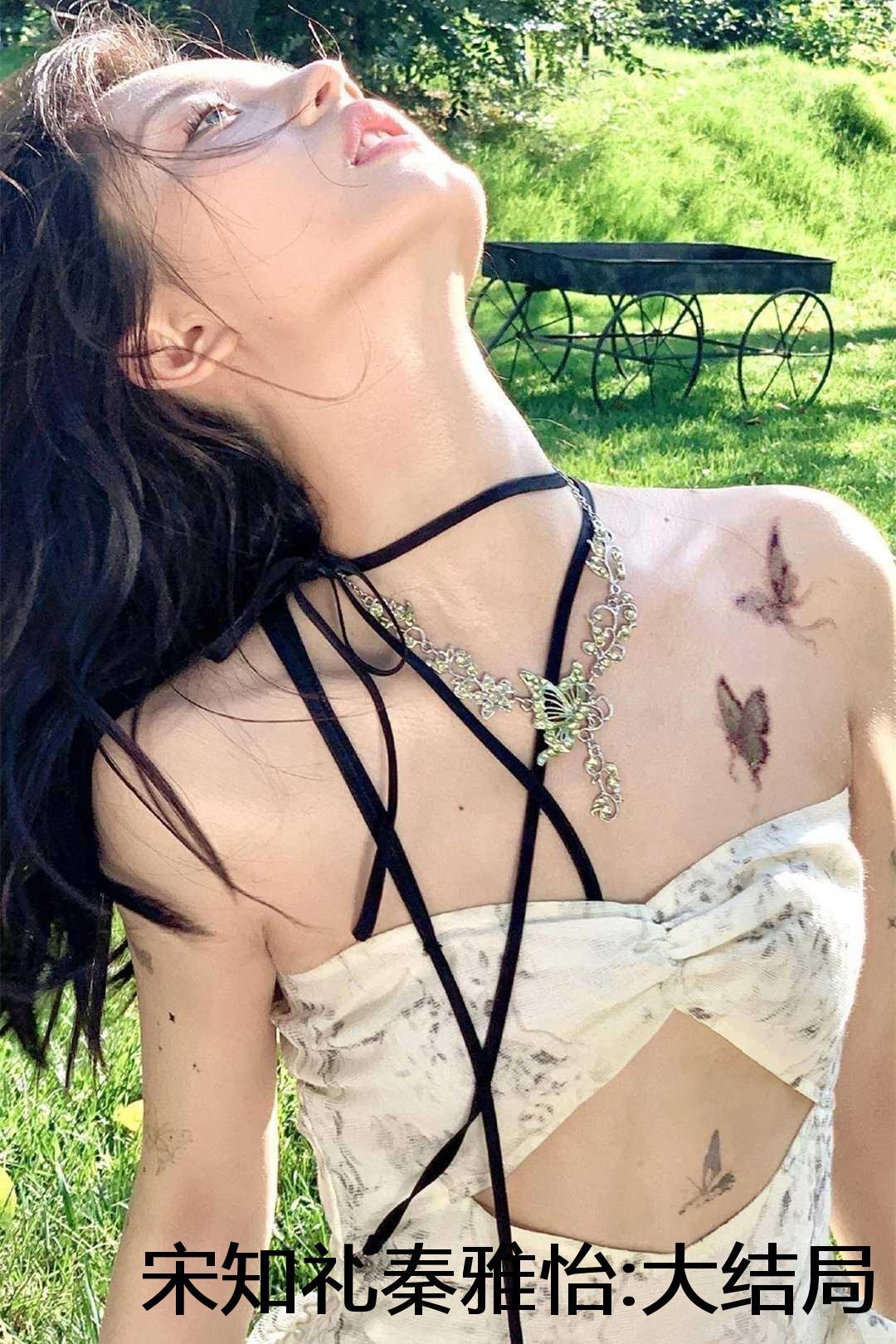
![盗版万人迷[快穿]](/img/478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