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小说>穿越后他成了救世主 > 第 38 章(第2页)
第 38 章(第2页)
“你怎麽这麽不禁吓呀。”他拧拧眉,不快,“站那儿,我过去。”
“你不吓我就好了。”我嘴很快,把在他身上感受到的能和橘御木叠上的理所当然的口吻抛诸脑後,不想怀疑他和大小姐有父女关系,“或者你回去,这样就不用再和我交谈了。”
他神色莫名地看着我,眼角的笑意一会儿显得古怪一会儿又很纯真。他怜悯地伸手拍我的脑袋。
霜山鸣玉微笑着说:“要是你能再聪明点就好了。——你还需要聪明吗?”
我噤了声。他也不再说话,只是挂着那种令人捉摸不透的笑容。
我晃晃脑袋,试图把他砸给我的东西扔出去。
我当然不需要再聪明了,人的一生没有那麽多需要的东西。聪明没什麽用,要是可以的话我愿意把它全部献给查理·高登,假装那是我请求他为我放在阿尔吉侬墓碑前的花——到那时阿尔吉侬也许还尚且不会有墓碑。
我想起每个晚上做的梦,夜夜都感到悲伤夜夜都无比平静。喜悦的片段在我脑海里如同走马观花,悲伤的情绪却宛如雕塑久久驻留。要是可以其实我没那麽愿意做一个傻子,但可以的话我情愿做一个傻子。
你说人生会有那麽多机会留给一个傻子吗?
我不知不觉把想的东西问出口,霜山鸣玉神情诧异,沉吟片刻後正色道:“如果傻子看得懂。”
我无声地笑,傻子要是能看懂那他就不会是傻子了。想这个没有用,我把蛋挞拆开一个给他,他站在原地慢慢把它吃掉,动作轻捷,比我的右利手还要迅速健壮几分。碎屑在他嘴边沙沙,他没意识到,我抽出纸巾给他擦。
他眯起眼,我才看清他的眼睛是竖瞳,冬日暖阳般的琥珀色。
“你为什麽会想穿一身黑?”
我把纸巾扔掉,问他。
“听别人说这样很酷,还有人说黑色很严肃。”他一本正经的,“我以为第一次见人都穿这个样子,没想到你好像不这麽觉得。”
他打量我,从头顶扫到脚上的鞋:“不过别有意趣。”
如果白色短袖配黑色长裤也算意趣的话。九十点钟的时候太阳很热,所以我特意没带外套。什麽时候到深冬?我是不是该买棉袄了?天上的云真漂亮。路有点硌脚,之前没硌脚啊?路径在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对话里被缩短,校门近在眼前,银杏树还和见到顾行涟的那天一模一样。
霜山鸣玉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我听说人的奶茶很好喝,你也想喝吗?”
我毫无波动地:“没有。”
我问:“你还准备进学校吗?”
“想啊,能和你待在一起,什麽地方我都会愿意去的。”他嘴上这样说,闪烁着狡黠的光的眼睛却在讲别的。我欲言又止地看了他几眼,他自鸣得意地对着我:“我终于吸引到你的兴趣了吗?”
我平静地点点头,整理了短时间内发生的所有事,明白他从始至终都只是在逗我玩,好在没有伤害到任何人:“那你走吧。”
他有些惊讶,眼睛瞪得溜圆:“你为什麽想让我走呢?只要你想,任何地方我都可以陪着你。”
看上去很不解,连自带的狡猾都消失了。
“霜山先生,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我有些烦躁,没人知道它从何而来。飞速闪过的思绪让我觉得它无比重要,我想起一会儿得喝水。
然後我才说:“时间并不为我们一时的分别而停留它的脚步,该见面的话就会见面。”
是这样。
对于一个骗子来说。
我不知道它的真名,不知道它是用什麽手段迷惑的房东阿姨,也不知道它是否真的只是从附身橘御木的时候才开始对我感兴趣。我不介意成为傻子,唯一介意的是那块蛋挞。我以为我和它确实可以摒弃前嫌,比如我可以借着身体接触的过程把种子一点点拽出来。
我得让橘御木再注意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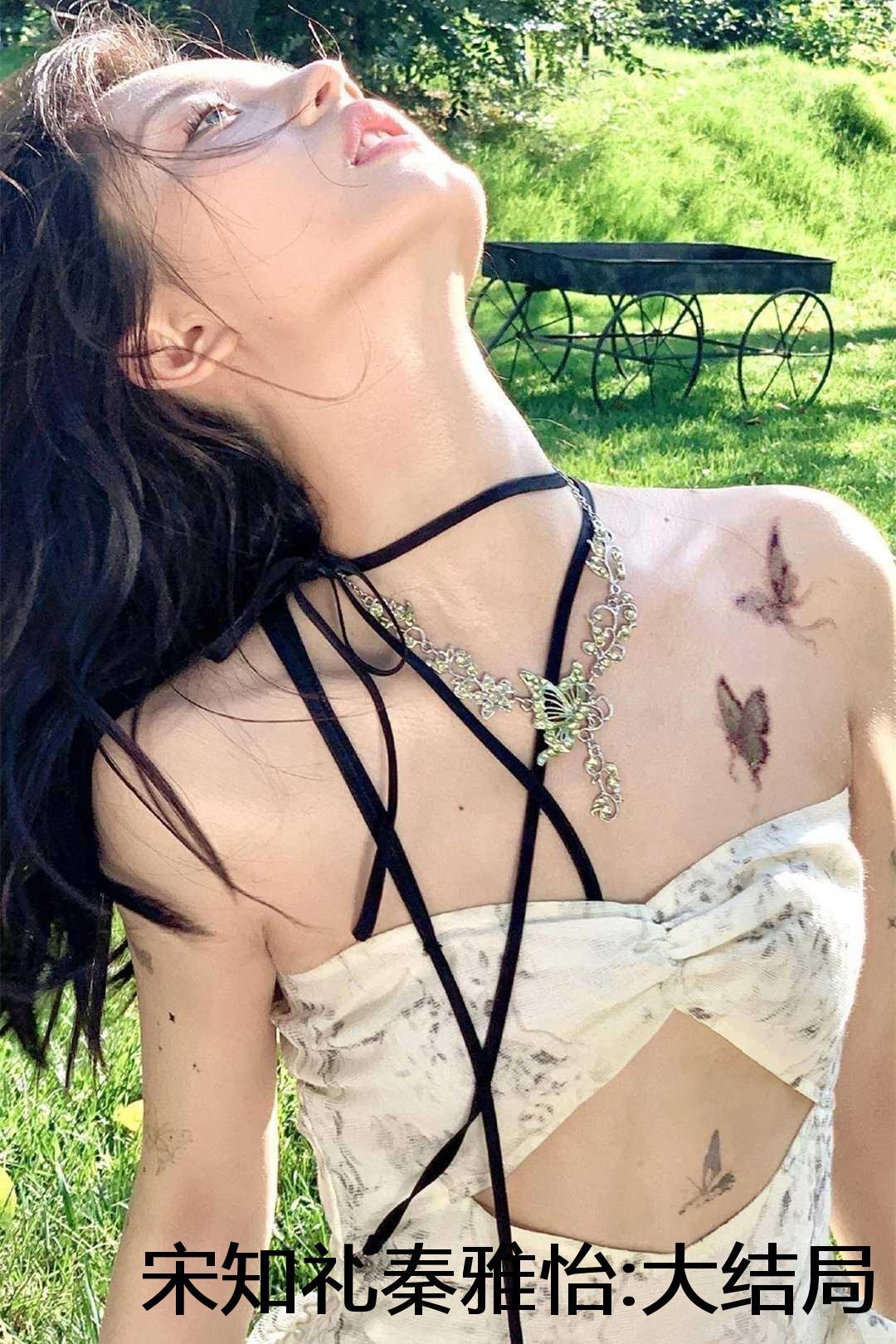
![盗版万人迷[快穿]](/img/478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