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小说>希腊神话 恶魔 > Chapter52(第2页)
Chapter52(第2页)
她想起当年被迫点头应允婚事时,殿外飘着和今日一样的冷霜,想起无数个深夜,她独自在书房处理政务,而梅尔却在後宫饮酒作乐。
他没有承担起丈夫的责任,也没有承担起父亲的角色,更没有为国家和子民付出过贡献。
她对他并无感情,她需要的是王後的身份,可以照顾她可爱的莫伊丝。
现在,缘帖碎了,那些束缚也该碎了。
“梅尔。”
弗兰终于转头看他,语气平静却带着前所未有的疏离:“我有没有好日子过,从来都不取决于你,更不取决于这张缘帖。”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殿内衆人。
“至于斯图亚特,它容不容我,该由子民说了算,由莫伊丝说了算,唯独轮不到你这个算计亲生女儿的僞君子置喙。”
赫拉看着弗兰,语气里多了几分认可:“缘帖已解,从此你与梅尔再无婚姻羁绊,往後人生,皆由你自己做主。”
弗兰轻轻舒了口气,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
她擡手抚了抚心口,那里再也没有了以往那种隐隐的束缚感,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轻松。
莫伊丝看着她眼底的光亮,忍不住握紧了她的手,声音里带着笑意:“弗兰阿姨,以後我们一起,把斯图亚特守好,会过上好日子的。”
“疯子!都是疯子!”
梅尔看着消散的金光,彻底瘫坐在地上,眼神涣散,嘴里不停念叨着,“没了缘帖,你什麽都不是……什麽都不是……”
凯撒琳收回长刀,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对身旁的死侍道:“把王夫梅尔带下去,关押在禁宫,没有王女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探视。”
“凯撒琳,不必。”
少女手腕骤然用力,帽针插进了梅尔的喉咙,用尽了全身力气刺断皮肤,闷闷道:“您在位十六年,逼迫凯撒琳一介孤女,偏信内阁那些老狐狸,把斯图亚特的土地割给邻国,把百姓的赋税堆成您酒池肉林的砖瓦。”
“您忘了母亲临终前嘱托您护好家国,忘了您对着祖父的牌位发誓要让子民安居乐业,您只记得您的权力,您的享乐,您的昏聩。”
“君父,该下地狱了。”少女贴近男人的耳边轻轻道:“母皇会为我感到骄傲的。”
伴随着沉闷的落地声。
那颗曾象征着至高权力的头颅滚落在地,眼睛还圆睁着,似是不敢相信自己会死在女儿手中。
鲜血溅在莫伊丝的脸颊上,温热的触感让她浑身一颤,却没有松开帽针的手。
她擡起头,望向殿外。
初晨的晨光正透过云层洒下来,落在积满尘埃的宫墙上。
身後传来脚步声,弗兰提着干净的帕子走上前,轻轻为她拭去脸上的血污,声音里带着心疼,却也藏着止不住的欣喜:“做得好,莫伊丝。”
“从今天起,斯图亚特,该换一种活法了。”
莫伊丝的加冕礼选在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是北境难得的好日子。
那些常年凝结着霜花的冰雕,此刻竟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与广场上挤得水泄不通的子民们呼出的白气交织在一起。
人们踮着脚,裹紧了羊毛斗篷,目光却死死锁着高台,连冻得发红的脸颊上,都刻满了近乎虔诚的期待。
这是属于他们的新君主,是霍桑女皇的女儿,是契斯科的希望,是斯图亚特的未来。
莫伊丝身着绣满金纹的白色皇袍,宽大的衣摆拖过台阶,每一步都走得沉稳。
她的黑发被盘成精致的发髻,仅用一支珍珠帽针固定,没有过多华丽的装饰,却难掩周身的锐气与温柔,像寒冬里初绽的雪绒花。
走到高台中央时,她转身面向百姓,目光扫过一张张带着希望的脸庞,老人浑浊的眼里含着泪,孩童举着小小的旗帜蹦跳,还有护卫们挺直的脊梁……
莫伊丝不自觉地握紧了腰间的剑柄,那是母亲霍桑留下的佩剑。
今日她将带着这份传承,履行自己作为女皇的职责,接下那副沉甸甸的担子。
弗兰手中捧着镶嵌着绿宝石的金质冠冕,蔷薇色的衣裙在微风中轻轻飘动,母性光辉让她看起来愈发庄严。
她看着眼前的少女,从当年躲在自己身後的女童,到如今能独当一面的女皇,时光在她身上留下的不是怯懦胆怯,而是历经风雨後的坚定。
“莫伊丝·契斯科。”
弗兰的声音传遍广场的每一个角落。
“你是否愿意以生命守护这片土地,以公正对待每一位子民,以智慧勇敢引领斯图亚特走向光明,无论繁荣或苦难,永不背弃你的誓言?”
莫伊丝莫伊丝微微屈膝,皇袍的衣摆在此刻划出优雅的弧度。
“我愿意!”
“直至契斯科的鲜血不再流动,我永不会背弃我的子民,我会如同我母亲一样,守护斯图亚特的未来!”
她的声音不算洪亮,却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广场上瞬间响起雷鸣般的欢呼。
弗兰上前一步,小心翼翼地将冠冕戴在莫伊丝的头上,金冠的重量压在头顶时,莫伊丝没有丝毫动摇。
绿宝石的光芒落在她的黑发上,与银制帽针的微光交织,竟让她眉眼间的稚气渐渐褪去,多了几分君主独有的威严,仿佛这顶冠冕本就该属于她。
皇冠只为真正的继承人闪耀。
“从今日起,你就是斯图亚特的女皇。”
弗兰的手落在莫伊丝的肩头,轻轻将她扶起,掌心的温度透过皇袍传过来,像多年前无数个夜晚,她为莫伊丝掖好被角时的温度一样温暖。
莫伊丝直起身,擡手抚过冠冕,感受着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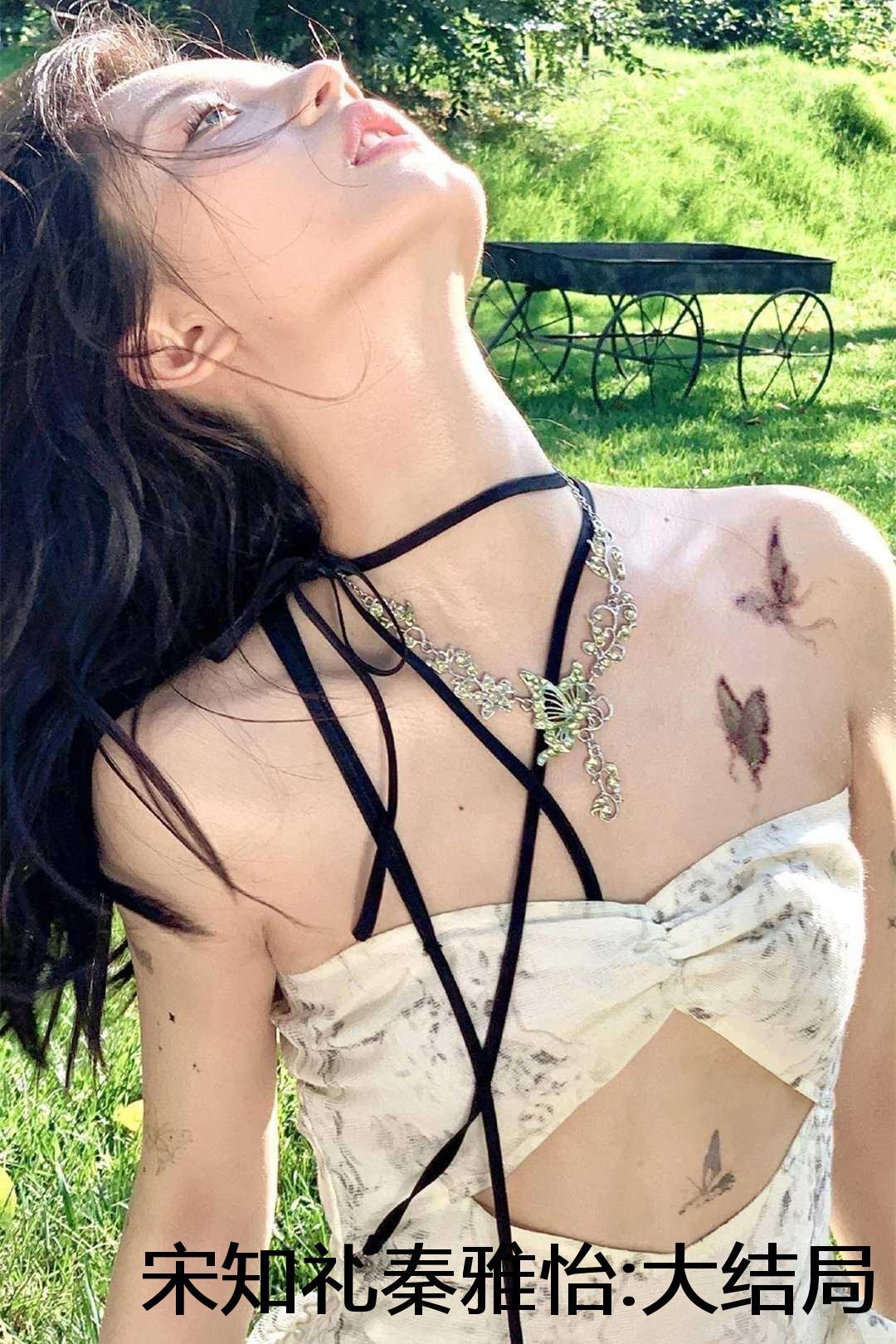
![盗版万人迷[快穿]](/img/478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