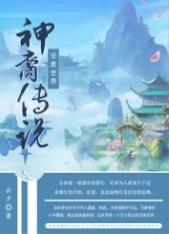富士小说>今天的马甲 > 第74章 数据洪流中的静默灯塔(第1页)
第74章 数据洪流中的静默灯塔(第1页)
夜色深沉,“拾光书屋”早已打烊,卷帘门落下,隔绝了外界。二楼公寓内,一片漆黑,唯有工作间角落的一台经过重度改装的服务器机箱,指示灯如同呼吸般明灭闪烁,出极轻微的、持续不断的低鸣。
苏晚坐在操作台前,脸上戴着防蓝光眼镜,屏幕的冷光在她毫无表情的脸上投下清晰的轮廓。她面前并排竖着三块大显示屏,上面不再是日常的图片处理软件,而是如同瀑布般飞滚动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代码流和数据包分析界面。
她放弃了直接登录暗网论坛寻找“architect”踪迹的冒险计划。那无异于在陆沉渊的眼皮底下点亮信号灯。
她选择了另一条更迂回、也更艰难的路——分析本地网络流量,尝试捕捉任何可能指向“architect”或与之相关的异常数据活动。
这是一个大海捞针的过程。城市的数字洪流每分每秒都以pb级的度奔涌,其中蕴含着无数正常与异常的信息碎片。想要从中筛选出特定目标的痕迹,需要惊人的耐心、算力,以及一丝运气。
她自建的这台服务器,算力远普通家用电脑,搭载了她自己编写的多个分析程序和算法模型,足以应对大部分非军用级的数据抓取和分析任务。
屏幕上,数据包被层层剥离、解码、分类。广告请求、软件更新、视频流、社交媒体信息……无数无用的数据被迅过滤丢弃。
她的目光锐利如刀,快扫过那些被标记为“加密”、“来源异常”、“协议特殊”的数据流。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屏幕上的代码依旧如同天书般滚动,似乎一无所获。
但苏晚没有丝毫急躁。她如同一个老练的渔夫,深知在深水中等待的价值。急躁是分析者的大敌。
她端起旁边已经冷掉的咖啡,抿了一口,苦涩的味道让她的大脑保持清醒。
忽然,一个极其微弱的、几乎被淹没在正常流量中的异常信号,触了她设置的一个特定过滤器。
信号非常短暂,转瞬即逝,使用的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几乎被淘汰的点对点加密协议的变体,传输的数据量极小,且源ip地址经过多层伪装,最终指向一个位于海外数据中心的虚拟服务器。
这种隐蔽而怀旧的技术风格,让她瞬间联想到了“architect”在论坛言中偶尔流露出的、对某些老旧但稳定技术的偏爱。
是她要找的目标吗?
无法确定。信号太微弱,太短暂,像幽灵一样滑过网络海洋,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供追踪的痕迹。
但她没有放弃。她立刻调整了分析参数,缩小捕捉范围,将重点放在这种特定协议变体和类似的数据特征上,同时调动更多的算力,试图在海量数据中再次捕捉到它的身影。
等待。依旧是漫长的等待。
屏幕上,数据洪流依旧奔涌。
就在她以为那次信号只是偶然的干扰时——
又一个类似的信号出现了!同样微弱,同样短暂,源ip再次变化,但加密协议和数据特征高度吻合!
这一次,信号出现的时间点,与第一次相隔了大约二十三分钟。
像是一种心跳,一种极其规律的、小心翼翼的脉搏。
苏晚的精神瞬间高度集中。她快记录下两次信号出现的时间戳、伪装ip、以及所能解析出的微量数据特征。
她尝试进行反向追踪,但对方的反侦察能力极强,路径上布满了陷阱和误导,几次尝试均告失败,反而差点触对方的警报系统。
她果断停止了追踪尝试。打草惊蛇是愚蠢的。
她的目的不是立刻抓住他,而是确认他的存在,了解他的模式。
两次信号,间隔二十三分钟。这是在送心跳信号保持连接?还是在接收或送极其微量的指令、状态报告?
数据量如此之小,说明传递的信息极其精炼,可能只是代码、坐标或者简单的状态标识。
这种谨慎和高效,符合她对“architect”的侧写。
她将这两个信号的出现坐标(经过粗略地理定位,大致都在本市区范围内,但无法精确)和时间戳输入另一个分析模型,试图寻找其活动规律与其时间段内本市生的其他事件的关联性。
模型需要时间运行。
她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眉心。长时间专注屏幕让眼睛有些干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