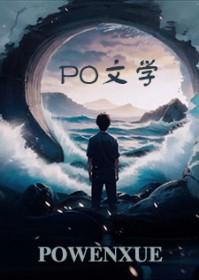富士小说>今天的马甲 > 第82章 镜像囚笼与告别的姿态(第1页)
第82章 镜像囚笼与告别的姿态(第1页)
工作间的光线调整到一种恒定的、模拟自然光的状态,忽略掉窗外真实的昼夜交替。苏晚坐在其中,如同置身于一个时间凝固的实验室。她的面前,并排运行着多个屏幕:电网实时波动频谱、被隔离主机镜像的状态监控、以及她正在编写的复杂控制程序界面。
她要创造一个“数字幽灵”,一个在她离开后,仍能在这间屋子里“生活”的“苏晚”。
这个幽灵需要能够:模拟她的用电习惯(特定时间亮灯、电脑开机、饮水机加热),生成符合她行为模式的网络流量(浏览摄影网站、查询旅行信息、处理图片),甚至……通过那个物理窃听器,播放出预先录制好的、充满生活气息的环境音——翻书声、脚步声、烧水声、偶尔哼唱的旋律片段。
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能够接收、识别并响应通过电网送来的特定激活信号(如果“architect”或其同伙再次尝试用音频密钥激活木马的话),并反馈回相应的、看似正常的虚假数据。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硬件控制、软件模拟、音频欺骗和协议逆向。她几乎调动了所有可用的技术和算力资源。
她精心编写了数日的“日常脚本”,细化到每一个小时可能产生的声音和能耗。她录制了长达数十小时的环境音素材,并进行降噪、混响处理,使其听起来像是在不同房间位置、不同时间点自然采集的。
她甚至编写了一个简单的ai学习模块,让它能够基于她过往的本地网络活动记录,生成不那么规律、更具随机性的虚假网络请求,避免过于程式化而被识破。
最难的部分在于与电网信号的交互。她需要确保她的控制设备能够精准捕捉到可能从电网中传来的、极其微弱的激活信号,并能即时通过调制电流波动的方式,将编造好的数据送回去。
经过无数次测试和调整,一套被她命名为“镜像囚笼”的系统终于初步搭建完成。
她进行了一次全系统模拟测试。程序启动,工作间的灯光按照脚本明灭,音响里播放出精心编排的“生活声音”,网络流量模拟器开始工作,电网信号调制器也处于待命状态。
她站在房间中央,冷眼看着这个自己创造的、没有灵魂的“日常”景象。声音逼真,灯光自然,数据流看起来也毫无破绽。
但这逼真的表象之下,是完全的虚假和受控。
就像一个极其精美的玩偶屋。
她关闭了系统。房间瞬间陷入一片死寂。
一种难以言喻的冰冷感包裹了她。她正在用自己的技术,为自己编织一个囚笼,用以欺骗那些无形的监视者。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作茧自缚?
但她没有选择。这是目前最能保障她离开后后方稳定,并能反向迷惑对手的策略。
距离出去巴黎的日子越来越近。
她开始公开地做出一些符合“人设”的准备工作:去图书馆借阅法国旅游指南和摄影画册(并在借阅记录上留下痕迹),向叶蓁咨询穿搭建议(并让对话被可能存在的监听捕捉),甚至在一次“偶然”的邻里闲聊中,“不经意”地透露出要出国参加活动的消息。
她表现得像一个对即将到来的旅行充满期待、又略带紧张的普通女孩,完美地扮演着陆沉渊和“architect”可能期望看到的角色。
出前三天,她接到了一个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电话。
看来电显示,是陆沉渊的私人号码。
苏晚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眼神微凝。该来的总会来。
她让铃声多响了几声,仿佛刚从什么事情中回过神来,才接起电话,声音里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意外和拘谨:“陆总?”
“苏小姐,没打扰你吧?”陆沉渊的声音一如既往的低沉温和,听不出任何情绪,“听说你要出国参加一个摄影比赛?恭喜。”
消息果然灵通。苏晚心中冷笑,语气却带着点不好意思的欣喜:“谢谢陆总。就是一个很小的比赛,运气好入围了,去见识一下。”
“巴黎是个好地方,很适合摄影创作。”陆沉渊仿佛闲聊般说道,“行程都安排好了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在那边也有些朋友。”
试探来了。想掌握她的具体行程?还是想“安排”人“照顾”她?
“都安排得差不多了,组委会提供了酒店和行程。”苏晚连忙拒绝,语气带着不想麻烦别人的疏离,“谢谢陆总好意,我自己能行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两秒,然后陆沉渊轻轻笑了笑:“也好。出门在外,多注意安全。最近国际航班也不太平静。”
他的语气听起来像是普通的关心,但“不太平静”几个字,却似乎带着一丝若有深意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