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小说>主神的无限世界编辑器 > 第6章 特殊实践课 欲望的分类样本2(第1页)
第6章 特殊实践课 欲望的分类样本2(第1页)
菊花,是人体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门”。
它不像小穴那样,天生就为了容纳和吞吐而存在。
它是由两圈强劲的、终年紧缩的括约肌守护的、绝对的“禁区”。
想要征服它,就必须用最原始、最野蛮、最不讲道理的暴力,将其彻底撕裂、撑开、蹂躏,直到它忘记自己原本的功能,变成一个只会为了迎合主人而张开的、淫荡的肉洞。
此刻,我正在进行的,就是这样一场神圣的“开光仪式”。
墨影那具高挑而充满韧性的身体,在我的胯下剧烈地颤抖、弹动。
她的十指,已经深深地抠进了身下的羊毛地毯,指节因为用力而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惨白。
她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此刻已经彻底被痛苦和屈辱所扭曲。
汗水、泪水,混杂在一起,将她额前的黑浸湿,狼狈地贴在脸颊上。
她的惨叫,是那么的凄厉,那么的绝望。
这声音,与她平日里那种“生人勿近”的冷漠气场,形成了最鲜明、也最刺激的对比。
这声音,对我而言,比任何春药都更有效。
“叫吧,墨影,大声地叫出来!”我一边狞笑着,一边抓着她那纤细却富有弹性的腰肢,开始了对那朵处女之菊的、血腥的开垦,“让所有人都听听,我们学校最高冷的冰山女神,在被人用一根又粗又长的大鸡巴,狠狠地、不带任何润滑地操着屁眼的时候,叫声是多么的淫荡,多么的悦耳!”
我的巨根,在她的体内,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极致的考验。
太紧了!
紧得乎我的想象!
肛肠的构造,与甬道截然不同。
这里没有天生用来容纳的弹性,也没有爱液的润滑,有的,只是无数层坚韧、干涩、如同铁箍般的环形括约肌,以及密密麻麻的、比甬道敏感无数倍的痛觉神经。
我的巨物,在进入的那一瞬间,便遭到了最顽强、最疯狂的抵抗。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我那硕大的龟头,正被那些从未被扩张过的、紧致到变态的肠壁,死死地、疯狂地、痉挛般地绞杀着。
每一次微小的寸进,都像是用砂纸在反复打磨我的马眼,那种酸胀、麻痹、几乎要被夹断的剧痛感,让我爽得差点当场射出来。
而对于墨影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地狱般的酷刑。
我能感觉到,我的龟头顶端,已经撕裂了她那层薄薄的肠道黏膜。
温热的、带着腥味的鲜血,瞬间就从那被蹂躏的伤口处渗了出来,成为了这场野蛮“开苞仪式”中,唯一的、也是最刺激的润滑剂。
“痛……好痛……杀……杀了我……呜呜呜……求求你……”
她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此刻已经彻底被痛苦和泪水所淹没。
她的身体,如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女,在我的身下剧烈地弹动、挣扎。
她的指甲,深深地抠进了身下的羊毛地毯,仿佛要将那里撕裂,来泄那无处可逃的、撕心裂肺的剧痛。
“杀了你?呵呵……”我狞笑着,非但没有怜悯,反而更加兴奋了。
我喜欢她现在的表情,喜欢她这副被我彻底玩坏、引以为傲的冷静荡然无存的模样。
我俯下身,张开嘴,狠狠地咬住了她那因为痛苦而剧烈颤抖的、线条优美的蝴蝶骨,用一种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魔鬼般的声音,在她耳边低语
“你不是很能装吗?不是很喜欢摆出一副与世隔绝的死人脸吗?现在怎么不装了?叫啊!大声地叫出来!让所有人都听听,冰山美人那高傲的屁眼,被一根又粗又长的男人鸡巴,活活操烂的时候,出的声音,是多么的……美妙!”
我的话语,如同最恶毒的诅咒,彻底击溃了她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啊啊啊!你这个……魔鬼!混蛋!”
她终于放弃了抵抗,开始放声地、歇斯底里地咒骂、哭喊。
而她的身体,也因为这情绪的崩溃,而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变化。
那原本如同铁壁般坚韧、死死抵抗着我的肠道,竟然……竟然开始微微地、不受控制地放松、软化。
我知道,时机到了。
“这才对嘛……我的小冰山。”
我狞笑着,腰部再次力,将我那根已经没入了一半的、沾满了她鲜血和肠液的巨物,在一声粘腻的、如同烂泥般的“咕啾”声中,毫不留情地、整根、没柄、一捅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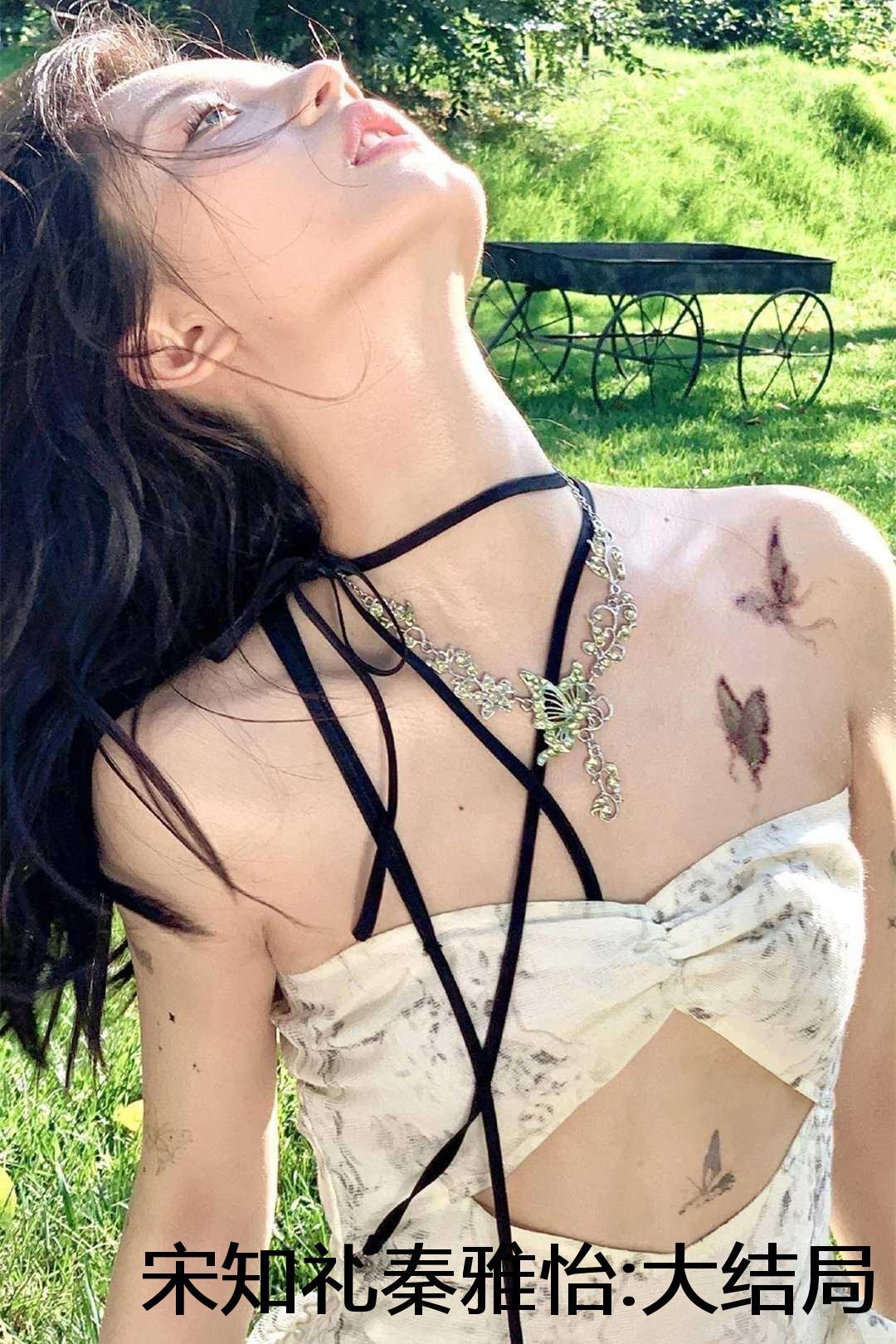
![盗版万人迷[快穿]](/img/4789.jpg)